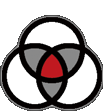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提问“意派”:从我的经历出发 |
朱金石
1988年,我和秦玉芬在柏林居所分别完成了第一件装置作品。借此,我们约邻居,美国观念艺术家牛顿•海瑞森夫妇一起组织了一个聚会。这一天来的客人几乎都是居住在柏林的各国“海外精英”,有些客人直到今天依然与我们一见如故。我和秦玉芬在这个聚会中做的作品非常简单:她在一面墙上先贴了一层柏林报纸,之后在报纸上又裱糊了一层宣纸;我则在另一个房间用几根方木料组建了一个架子,架上叠搭上十几米白色画布,然后用剪刀把这些画布剪成书本大小。这两件作品开始了我们在当代艺术上的尝试。它们是什么呢?它们有什么意味?当时,在我们自己还不完全清楚时,至少有一个人意识到了什么,他是博伊斯的朋友与支持者瑞内•布洛克。他看了作品后开始支持我们,并在几年间排除异议,给我们提供机会。他是柏林艺术界权威人士,这次也来看我们在柏林公寓组织的小展览,我当时问他,你怎么会来?他回答,展览不分大小,不分地点。
谈“意派”,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往事,我不禁问自己,这场景是不是有点“意派”?这一问有些意外,如果身临其境,事情大概会变成另一种意思,譬如,当时我们如果说我们是“意派”,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惊奇。我们在柏林认识的朋友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接触中国艺术家,他们直到今天对我们仍保持着好奇。2008年年底,我又和这些朋友在柏林见面,他们继续和我讨论中国,讨论中国艺术。这时,我的变化非常大,二十年前,我拼命地想解释自己,解释中国的艺术,但解释不清;现在我避开解释,发现问题清楚了。谈“意派”使我想到我自己艺术体验中的变化,继而想象二十年后人们会如何谈论“意派”。
这里引出了几个话题。其一,假如我和秦玉芬1988年的作品在当时被称为“意派”,将会发生什么?其二,面对“意派”,我们假如给它二十年的时间(或者是过去或者是未来),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三,“意派”和中国现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关系?思考最后一个问题应该是最根本的。许多中国艺术家的艺术从一开始就和西方艺术不太一样,这种“不太一样”在他们的作品中顽强地保留至今,但在1980年代末期,这种艺术现象受到诸多限制,又或者说刚刚处于初始状态。多年之后返身观看,这些艺术家的艺术区别尽管很清楚,但隐约之间又有一个一致之处让这些艺术家向一个方向移动。一致之处是什么呢?“意派”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意派”研究的是这个一致之处的某一个现象,譬如中国的海外艺术现象,它就会寻找一个清楚的流派;但如果研究的对象是从1970年代至今发生的艺术现象,它的对象就会是诸多流派。一种理论的意义显然不会因为对象的大小和多少而产生缺失,重要的是一种理论是否能够针对它的研究对象提出合理性的观点。
1988年柏林组织了一个大型日本艺术节,这一年,我和秦玉芬知道了“物派”并开始追踪它,而且非常警惕,不希望我们的作品和“物派”相提并论。当然,我们都很崇拜几位前辈日本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带着亚洲的旋风,迷醉了欧洲的艺术界。此时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还未出场,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正在筹备之中,今天“意派”理论的创始者高名潞正是这个大展的风云人物。可是,我和秦玉芬1988年在柏林想些什么?大概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是艺术”。我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判断就不动手的艺术家,所以,1988年至1990年,我的艺术工作就是苦思冥想。最后,终于整理出自己的一些观点:一、无形的形超然于有形的形;二、东方思想的神秘主义是中国艺术的主体;三、非艺术是艺术中的艺术。这三个结论不是理论,而是具体的艺术实践。1994年我回到北京之后,这种实践依然继续,并且和几位年轻艺术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当时的作品如果是“意派”,那“意派”一定很飘荡。记得一次我和王蓬、宋冬、尹秀珍等几位艺术家去了大觉寺后面的山里做作品,我把一张宣纸铺在了湖面上。我的这种行为是艺术吗?今天一些朋友非常欣赏我这个时间的作品,为什么?他们喜欢的理由是什么?和“意派”有关吗?如果与“意派”无关,那它是什么?激浪派?物派?还是极少主义?或是观念艺术?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在西方艺术领域中产生影响力,但西方艺术界很难把这种现象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关联起来,他们认为中国艺术家是掌握了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念方法,关键只在于使用了东方的材料。但是,他们在看日本艺术时却通过“物派”将日本当代艺术的源头确认为东方精神、东方传统。正是因为中国海外艺术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挑衅、颠覆西方中心主义艺术的诉求显然远远超过日本当代艺术家。也正是这种原因,1990年代的中国海外艺术一直保持着与“物派”的明显距离,譬如,黄永砯在西方“现场”对西方社会问题的“挑衅”艺术,在日本“物派”艺术中根本无法看到。
所以,“意派”的出现首先与对抗西方艺术系统有关,但这种对抗是建立在对西方艺术流派分析的基础上的,并对西方当代艺术的思想、哲学、美学做了深入的研究。我之所以极为关注“意派”,是因为在长期观察西方艺术流派的过程中总有许多不解,高名潞对抽象表现主义、极少主义的理论分析使我终于豁然开朗。我想,如果没有长时间的艺术实践,没有对西方艺术流派的直接观察,理解高名潞的理论会产生雾里看花的困惑。正是这种原因,或许我的实践与体验会帮助大家增加一个角度,进而参与到“意派”的讨论中来。
2009年今日美术馆的“意派”展览中,有几件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何云昌将日常劈柴作为自己的一件作品取名《出入》,焦兴涛的《风景》塑造了一个不可攀爬的天梯,还有隋建国的《时间的形状》和梁绍基的《沉钟》等,这些作品有一种相互关联的感受。但有趣的是肖鲁的《作品1、2号》、秦玉芬的《禁锢》、蔡锦的《美人蕉292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如果把上述作品提取出来做一个展览来看“意派”会产生什么印象?似乎男性艺术家的作品都是在含蓄中释放一种力量,而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则是在直接的视觉动力中隐藏着内心的某种东西。这是“意派”现象吗?或者说“意派”通过展览在一个特殊的层面上向我们诠释出中国社会中男女性格、气质、感觉、精神之间的差异?如果是这样,这种差异有什么启示?由此可以引发出什么样的思考?如果是“意派”,“意”在什么地方?如果这样追问下去,这将不仅仅是艺术领域的现象,可以更大范围地展开。当然,上述提出的看法并非是“意派”的核心理念,它只是以拓展的意图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意派”的意义。而高名潞也正是通过“意派”的方法论从视觉艺术之外拓展“意派”理论的视野,并对社会形态等问题展开了尝试性的讨论。“意派”理论源于对视觉艺术的思考,但思考的视野又远远超越了艺术的边界。
1978年,周迈由有一天不知为何一定要画大画,但在这之前,他几乎没有在大画布上画过画。去哪找如此大的画布?迈由心意已定,就扯来自己的床单,把它用图钉钉在鼓楼西大街70号的一间平房的东墙上,这是我们家的墙,我母亲居然接受了这个现实。迈由开始画了,画的过程中又来了另外一位年轻艺术家,就是今天的王鲁炎,他画周迈由画这张画的场景,我们家乱套了,我忘记这时我在干什么,估计在应对有些混乱的局面。但终究在我们家里的动静很小,一年之后,星星画会在美术馆馆外展览前的几个星期,这幅画与迈由的另外几件作品居然出现在西单墙上。迈由真是疯掉了。或许星星画会的出现救了迈由,在大局面下,迈由的问题成了小问题,但星星画会在美术馆外的展览是否受到迈由的启发不得而知。总之,三十年后,这件作品静静地置于“意派”展览中的一面墙上不泛波澜。但是,“意派”选其作品至少不是因为视觉上的美感,不是因为和中国传统美学的关系。这件作品的“在野”特征、反学院特征、反意识形态特征,无论从今天73岁的周迈由的艺术生涯看,还是从当时特殊年代的北京去观察,都无疑体现出“意派”理念中的社会性是非常清晰和有力的。“意派”并非是一种对中国历史美学的讨论,而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当代艺术中的社会语境提出了异于他者的主张,其实,稍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从“意派”展览中发现这样的案例。
1997年,我这个没人感兴趣的艺术家突然得到一个机会,温哥华国家美术馆对我的宣纸装置作品感兴趣,在我访问了温哥华看了场地之后,提出要在美术馆不曾做过作品的大厅做一件作品。这件最终实现的作品名为《宣纸道》,五百刀中国运去的宣纸被温哥华人揉过展开,一张一张地铺在一个特制的铝合金架构上,然后小心翼翼向23米高的大厅顶端升起,然而,几吨重的宣纸悬挂在大厅中部显不出重量。美术馆项目负责人戴娜(Daina)女士这样描写到:“艺术家通过含有意义的名称赋予自己作品独特的关联,进一步摧毁了古典极简主义风格,他在唤起极简主义美学的同时,强调精神性是最根本的基石。”我在1990年代中末期的作品或许和西方60年代的极少主义拉开了距离,但是,我的作品与“物派”的关系是什么?其实这个正是今天“意派”被质疑的一个问题。在回忆1990年代的艺术中,我与学者汪晖在对话时讲到:“日本物派以纯化的东方精神静态地进入西方当代主义的想象,而中国的海外艺术则以咄咄逼人的侵犯方式,借用西方观念,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
直到今天,我对日本“物派”艺术依然保持着敬仰之情,“物派”与日本文学、音乐、电影在1980年代前后影响了整个世界。在亚洲当代艺术潮流中,它以谦虚的姿态率先进入全球的视野,并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1988年我在反思艺术时,手中只有铃木大拙的一本小书,但它却给了我奇异的力量。正是由于我对“物派”的尊重,我一直观察中国当代艺术中有没有“物派”,我的观察让我失望。“意派”理论的出现给我带来新的思考。首先,我发现中国艺术家与中国传统文化都似乎具备“物派”的土壤,但是,艺术家与社会在现实中的冲突又使这种机遇成为一种不可能。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与“文革”有关。“文革”一下断裂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而“物派”的一个最本质的核心是尊重传统。但是,今天整个亚洲离自己的传统愈发远去。我认为,假若“意派”与“物派”真的难辨雌雄,那么,“意派”的主旨应该不是被批评,而是应引起慎重反思。西方全球化理论,解构主义理论无疑在特定的语境中有着难以抵挡的魅力,但是,“意派”是否能够给予我们一个新的当代信念?另外,如果把“意派”与“物派”联系起来比较,的确会发现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把“物派”与极少主义、贫穷艺术、大地艺术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在这些流派之间也有许多模糊不清的界限。譬如“物派”的第一件作品《状态——大地之母》,如果没有“物派”的理论,我们既可以把它看成是小一点的大地艺术,也可以看成是野外的极少主义,或是使用自然材料的贫穷艺术。所以,如何把“意派”的理论、作品与其他理论、其他作品区别开来,既不能因为“意派”理论启用了中国传统美学就武断地定义“意派”是文化保守主义,也不能因为“意派”展览中的作品形态与其他艺术流派相似就简单化地认为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对他者的模仿。
今天,确认中国当代艺术的主体性是时代的需求,尽管,“意派”理论在学术层面上有待于长久的锻造,但其毕竟开创了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新路,而理论家高名潞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倾注在三十年间从未被各种困难阻挡过。如果是这样,我们必应以尊重的目光投向他持之以恒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对艺术的尊重应该投向何方?
(作者为自由艺术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