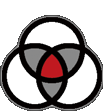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意派——世纪思维》 |
目录
第一部分
序言 高名潞 《“文化至上、 结构中西、整一存在”三位一体: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看“意派”》
第二部分
“意派记事”
第三部分
“意派——世纪思维”展览图录
第四部分
参展艺术家与作品信息
“文化至上、 结构中西、整一存在”三位一体: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看“意派”
高名潞
2007年我策划了《意派:中国“抽象”三十年》的展览,该展在西班牙巡回一年多之久。2009年5月我出版了《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一书,接着《意派:世纪思维》又在2009年5月底开幕。这三个事件不同程度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鼓励、批评和建议。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意派论的理论运用到艺术家的创作批评中。简单地讲,如何界定意派艺术和艺术家?
其实,这三个事件在我看来是一个整体,是理论和策划批评实践同时进行的工作。但是,每一步工作又有它的具体侧重:
1、 西班牙《意派:中国“抽象”三十年》以具体的艺术类型(所谓的中国抽象绘画)为例展开对意派的讨论,目的是把它和西方“抽象艺术”向区别,因为我们无法用现代主义情境中的抽象概念去界定中国过去三十年非写实绘画的本质和上下文。有关论述我已经在之前的文章中有所涉及,比如《中国极多主义》(2003)。在21世纪初的转型期,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上下文肯定具有自己的特点,其艺术生产也不同于西方,那么用西方现代主义的某种主义(比如抽象主义)去界定非西方世界出现的一种当代艺术潮流,注定是乏力和无助的。但是,要想建立新的批评叙事,必须首先具有新的叙事理论。那么就必须要在这些现成的西方先进理论之外,找到一个新方法和新角度,这就是我从“极多主义”到“意派:抽象三十年”所做的尝试工作。
2、 而《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一书的出版,则是从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不同于西方再现哲学的理论系统。《意派论》这本书是一个建树纯粹理论的尝试,不是针对具体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的批评文本。没有新的叙事理论,就没有新的批评。我期待将《意派论》进一步完善。
3、 在有了上述意派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树的初步工作之后,我又在今日美术馆策划了《意派:世纪思维》的大型展览。其重点在展示“思维”,而非风格。这次展览把中国当代老中青八十多位艺术家的作品汇集一起,从“人、物、场”的不同侧重角度去展示他们的“意派思维”。《意派:世纪思维》展览不是要勾画由几个艺术家所构成的风格流派,而是试图证明“意派”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方式,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具有普遍性。人们可能会期待用几个代表性艺术家和“意派”画等号,这个工作会在今后继续做,哪些成熟的艺术家体现了意派思维的不同侧面? 但这不是目前这个展览的目的。
但是,理论和策划实践同时进行必定会带来一些误解。这个误解还是纠缠在理论和艺术实践的关系上面。人们期待意派论不仅仅是理论,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且以此去评价当代艺术历史中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我在《意派论》一书,以及发表在《文艺研究》2009年10月号上的《意派的侧面》一文中都谈到了意派论的基本理论核心和观点。本文则试图把意派论放到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历史中讨论何谓意派。也就是说,我希望,意派不仅仅局限于艺术的风格和流派,它更应该是中国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它具有价值观、方法论和历史叙事等多重意义。所以,这个“历史意派”显然和我所陈述的意派理论有关,但是又有所不同。如果说《意派论》试图建树一个理论系统的话,那么“历史意派”就是中国20世纪以来那些具有意派论的思维角度和创作论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家。为了能更加具体地陈述说明它的历史,我将结合我自己过去多年的批评实践来讨论这个“历史意派”问题。
一、 把意派论放到现代性的历史中去讨论的可能性
我曾经在过去几年发表的一些文章和书中讨论了中国“整一现代性”的特点。在《意派论》一书中,我谈到了意派论的整一性,但是没有在现代性和中国现代艺术的历史逻辑方面充分展开对“整一性”的讨论。有人把“整一性”说成为政治的统一,精神的一致,这完全是误解。“整一性”的意思是契合地,非分裂地,运动非静止地看待历史和事物。
这个“整一性”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西方许多学者所描述的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即科学、宗教和艺术的分离和独立并不是中国现代性起源的特点。西方分离断裂的现代性必定引发极端反传统的革命断裂。相反,中国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提倡综合,比如,美育代宗教,艺术为人生,科学救国等。这导致“文化”成为一种“整一性”概念的代名词。“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都赋予“文化”一种超文化的意义,这可能和传统以来,中国人对文化的理解有关,文化往往意味着政治、道德和艺术的综合性结晶;其次,“整一性”的现代性视角提供了一种超现实时空的视角,就像胡适所说,“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绝对存在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境地,这个时间,这个我的这个道理。”[1]这里的道理、境地和时间就好像“理、识、形”,或者“人、物、场”三者的契合、整一,由此可以非常自在地面对世界去判断和选择,不论是中西还是古今都在超越历史时空的情境下自由选择;最后,整一性是一种文化态度,那就是从外观体用的“中西合璧”到内在整合的“结构中西”,这是中国现代性的必经之路。 [2]
中国现代性的启蒙可能不仅仅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和科学进步,同时也是文化整合。所以,“反传统”这个西方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的核心思想,其实并非中国现代性实践中的真问题,比如五四一代和八十年代的文学艺术虽然标榜现代和西方化,但是实际上重要流派和作品中都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因素。梁漱溟的那些似乎是保守主义的文化论点今天看来是中国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现代性文化遗产之一。文化的整合成为中国最早一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诉求,其代表是五四运动。[3]然而,这个理想被战争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所终止,直到文化革命以后的八十年代才再次复兴。但不幸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又一次中断或者延续了这个文化复兴的到来。但是,随着全球化、都市化的激进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传统体制的根本问题都会进一步暴露,我相信一个文化反省的新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中西合璧”乃至“结构中西”都需要假以时日,不可一蹴而就。但是,一部中国现代艺术史,基本是实用主义主导的历史,这是由于20世纪的革命和21世纪的都市全球化所引发的。中国现当代艺术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政治的遗产,不是人类最高文化的创造。这是文化的悲剧见证,因为与西方现代艺术相比,我们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个独特的现代性文化体系。遗憾的是,这种浅尝辄止的文化功能主义至今仍然是阻碍创造新世纪思维的根本障碍。文化思想不要服务于现实,它应当对人类的理性、智慧和人性价值负责。它永远是面对未来的,不是为现实和当下(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生活)的运作服务的。事实已经证明,倘若以当下为目的,那它将不断被现实所抛弃。
但是,五四时期奠定的“文化至上、结构中西、整一存在”三位一体的现代性始终在发展,并且在和实用主义的主流或者“高调艺术”对峙之中共生共存。显然,这和如何解读“五四”遗产有关。对于“五四”的现代性,从来就有不同的叙事,对此我有亲身体会。记得在1990年,当我的一位领导向我宣布停止我的工作并要求我在家学习马列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五四运动的核心是什么?”我不加思索地说,“科学与民主”。他马上批评我说,“你错了,是反帝反封建。”我无言以对,因为他说的也没错,那是自延安以来就有的“高调”主流叙事。
然而,恰恰是那种三位一体的“低调艺术”,或者“低调前卫”突出体现了意派的契合整一的文化价值观和艺术哲学,它也是一种中国现代性的价值核心。我相信,这个价值将在21世纪被充分发掘,尽管在20世纪它常常处于被压制和排斥的地位。
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的艺术史时,我们看到,“意派”的灵魂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性最初出现的时候已经诞生。而随着历史的推进,其外在叙事的方式也在变换,但是其内核没有改变。
二、 20 世纪初:未完成的“中西合璧”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不象西方现代性那样把道德、科学和艺术分离,而是将三者整一性地融合一起。 然而,道德、科学、艺术作为现代文化的分科也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性思考和实践,并且成为具体的艺术观和艺术实践的参照。 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中,道德、科学和艺术都是重要的现代性议题,而且经常混在一起谈。其中,现代性的道德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批判精神;科学现代性就是探讨语言层面上的现代化可能性,比如科学和玄学的嫁接;艺术的现代性则注重如何在艺术本体和本土性方面传承传统,试图在视觉上走出一条中国本土的美学逻辑。但是,当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讨论现代性问题的时候,他们经常把这三者融合互相替代地看待。事实上,中国早期现代性确实经过了科技(主要是军事和工业)、政治(戊戌变法)和文化(五四运动)现代化的三个阶段。中国人相信,只要把其中之一现代化,其他则迎刃而解。但是,先是军事的现代化导致了被不如自己现代的日本打败;百日维新的政治改革失败遂使中国知识分子(甚至举国上下)转而诉求文化现代化,从而催生了五四前后出现的“文化至上”的现代性。诚如陈独秀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我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指科学技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 [4]陈氏这里的“伦理”其实是广义的文化传统之意。所以,没有彻底的文化觉悟,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反省和认识,就不会有现代社会出现。
因此,在二十世纪之交,“艺术革命”的口号中被提到首要位置。首先冲击艺术领域的是以陈独秀、吕澂和鲁迅等人的“革命派”,要想请进“德”“赛”二先生,就必须“反传统”,革国画的命,就要移入西洋写实绘画的科学精神,他们取用外来,鄙夷文人画国粹,这种“不挑房盖就不会开窗户”的方法论上的偏激主张,实际上是基于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意识。这种对绘画史的反思是基于文化伦理这一民族精神的问题之上的。[5]
而“中西合璧”这种相对温和的主张也是出自对明清文人画传统的失望和批评,以及对艺术所承担的现代性责任的期待。然而,这些学者的“革命”也好,“中西合璧”也好,毕竟只能停留在思想上,真正的美学实践还需艺术家完成。于是,在艺术家那里,这个“合璧”就是探讨如何把东方的意境情绪与西方的现代主义形式相结合。
我们可以把20世纪早期的现代艺术大体分为三种类型:1、倾向于科学性“中西合璧”者,以林风眠、刘海粟、庞薰琴等为代表;2、倾向于道德更新者,以徐悲鸿以及左翼木刻版画为代表;3、倾向传统艺术美学的,以黄宾虹、高剑父、陈师曾、齐白石、潘天寿等为代表。三者都具有中西合璧的因素。 然而,除了左翼木刻外,所有这三种倾向都不走极端,相反都以自己的“反面”形式出现。比如,倾向于科学性“中西合璧”者实际上非常重视玄学性的“情绪”表现;倾向于道德理想者则注重科学写实;倾向于文人传统的则注重现实观察和感受。最终,三者都走向“非我之我”,而其中受西学影响的林、徐也都不同程度地回到传统。我曾经在1985年在《走向未来》发表的《中国画的历史与未来》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早期现代性中这种殊途同归的现象。
把科学的中西合璧融入中国现代艺术的理想在林风眠那里表述的最为清楚。 林认为西方艺术形式大于情绪,中国艺术情绪大于形式。林的“情绪”即是境界,是与现实和社会有关的情绪,他说:“西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向于客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过于发达,而缺少情绪之表现,把自身变成机械,把艺术变成印刷物。如近代古典派及自然主义末流的衰败,原因都是如此。东方艺术,形式上之构成,倾向于主观一方面,常常因为形式过于不发达,反而不能表现情绪上之所求,把艺术陷于无聊时消倦的戏笔,因此竟使艺术在社会上失去其相当的地位(如中国现代)。” [6]因此林风眠认为在吸收西方的科学性形式的同时要摈弃其机械性、模仿复制的反情绪的弊端,这样就可以避免中国晚期文人画过多强调情绪,反而流于个人消遣的弊端。所以,“合中西而为画学”意味着主要吸收西方的科学形式,但是旨在发扬“情绪”,这个情绪是现代的,于社会有用的。所以,林提出了“艺术为人生”的口号。但是,林的为人生,不是为现实,人生是指普遍人性和道德。
我们看到,在林风眠的早期绘画中确实有一种对人道主义的关注。这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反省。从一开始,林风眠所关注的就不是如何让艺术表现所谓的中国具体现实,而是如何使艺术成为表现纯粹人性的途径,如何建树一个理想的现代艺术境界和体系。在实践上,庞薰琴在30年代的创作与林的理想似乎更为一致。
相较于徐悲鸿有些“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艺术观,林风眠似乎更关注于永恒性的艺术,他的“中西合璧”是科学的艺术实验。他超越了视“写实即科学”的道德派的通俗伦主张。林风眠提出要“调合吾人内部情绪上的需求,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他从一开始就提出“从(中西)两种方法中间找出一个合适的新方法”,他的这种折衷调合态度主要是指以艺术手法去调合情感意蕴,是手法加情蕴的折衷宗旨,虽然中国画是情绪大于手法,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抒情表现这一要旨是不能削弱的。于是他自然而然地向西方现代绘画中的印象派、后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绘画中吸取手法,以补中国画手法之不足,因为,他认为中国山水画和印象派类似,也是以表现情绪为主,“所画皆系一种印象”。持这种意象表现宗旨的还有刘海粟、吴大羽等人,如刘海粟曾说:“画之真义在表现人格和生命,非徒囿于视觉、外鹜于色彩形象者,故画家乃表现,而非再现,是造型而非摹形也。” [7]所以,林风眠、刘海粟、庞薰琴和上海决澜社等艺术家正是在这个非再现的基础上得到了共识。如果我们把他们艺术中的情绪、人格和生命都放到“意象”这个范畴里,似乎很合适,他们的特点就是把情绪和印象完美结合起来。这个“意象抒情”就是早期中西合璧式的中国现代艺术的美学标准。
徐悲鸿提倡的是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不同于林风眠等人的“意象抒情”。徐悲鸿在未赴欧留学之前,就提出以西方科学的写实手法冲击和取代颓唐因袭的旧中国画。“西方之物质可尽术尽艺,中国之艺术不能尽术尽艺。”[8] “画之目的,在惟妙惟肖。”[9]如果说在留欧前徐悲鸿的写实主义还有较多的蒙胧的引进科学的因素,那么归国后的写实主义主张已是初具体系的信念了。他认为:“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壁,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也就是说,现代新绘画应该是科学写实的。而建立在再现现实基础上的写实主义才是解救中国艺术的唯一途径。
然而,徐悲鸿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完全忠实于外部世界(师造化)的现实主义,而是建立在道德至上的“形美论”美学基础上的“理想现实主义”或“象征写实主义”。简言之,就是“形美——道德美”统一论。这是传统儒家善即美、美即善的艺术观之延续。它不同于西方古典的“真、善、美”统一论。“真”在中国传统“尽善尽美”的哲学中并非核心价值。于是,在徐悲鸿的现代性那里出现了矛盾,既然科学写实是要表现“真”,那么他的写实主义就应当再现现实的真。然而,实际上它的科学写实并非为“真”而是为理想情绪服务的。1928年,与徐悲鸿共同创办“南国社”的田汉曾在《我们的自己批判——我们的艺术运动之理论与实际(上篇)》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悲鸿先生的所谓‘同’,虽耳目口鼻皆与人同,而所含意识并不与人同;他所谓‘真’,仅注意表面描写之真,而忽视目前的现实世界,逃避于一种理想或情绪的世界。”[10] 田汉认为悲鸿的画名曰写实主义(Realism),其实还是理想主义(Idealism)。这个评价无疑是非常中肯的。
我们只要将库尔贝的《石工》与徐悲鸿的作品相比较,即可发现,库尔贝对现实采取如实再现的态度,画家主体之情退居于现实场景之后,正如库尔贝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情节发生在烤人的阳光下,在道旁的沟边……这儿丝毫没有虚构的东西,我亲爱的朋友!我每天散步时都看到这些人。”而徐悲鸿则极力以主体情感意志干预现实场景,故现实场景也被作者强烈的理想情操和美性原则所规范,他的《徯我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和《九方皋》等作品,首先在题材方面就强调了象征因素,这种象征与民族抗战的现实有关,也和他的“天人”情操有关,“吾之所谓天人者”“指其负六尺之躯,其眉目口鼻之位置不与人殊,而器宇轩昂,神态华贵或妙丽,动用威仪,从容中道者;卑鄙秽恶者固不堪,亦无取乎来去飘忽变化万端如吴承恩、蒲留仙书中之人,纵自可喜非吾所谓天人也。”[11]
所以,林风眠的所谓“印象表现”和徐悲鸿的所谓“形美再现”其实都不过是传统“写意”表现的变体。[12] 然而,徐悲鸿的道德“形美论”与林风眠的科学“意象”论并非同道者。从现代性的角度看,尽管徐悲鸿的现实主义在国际背景下,并非现代艺术,但是,在中国的情景下,它和当时最为激进的、或者说最为前卫的左翼木刻运动以及毛泽东的延安木刻达成了共识。所以,无怪乎徐悲鸿说,是抗日战争让写实主义在中国发扬光大。所以,毛泽东的大众现实主义传统的早期来源,一个是徐悲鸿,另一个是左翼木刻。 而左翼木刻的直接来源是德国表现主义。所以,在接受苏联的现实主义之前,中国早期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相反具有极端强烈的主观性诉求。它的道德诉求又是文化功能主义与写实的混合体。它先天地具有实用主义的特点。
这种文化功能主义和道德现代性促使左翼文艺的青年奔向延安,投入了毛泽东的革命大众文艺。因为救亡和拯救大众确实是左翼热血青年的使命。这种情形似乎非常类似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前卫艺术积极参与苏维埃革命,以及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家参与墨索里尼的“革命”一样。不同的是,西方前卫艺术虽然具有革命的道德感,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艺术的“天真”性和不为大众理解的“精英”性。这在格林伯格那里称之为不媚俗。所以,俄国前卫最终离开斯大林的艺术系统。然而,去延安的左翼艺术家接受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整风洗礼,成为革命大众文艺的战士和政府的文艺官员。在不断把文化功能主义推向极端的过程中,艺术的知识分子本质和文化现代性的功能式微。革命领袖、光荣历史和幸福生活的三部曲成为千篇一律的题材。十月革命的俄国前卫崇尚革命,但是并不放弃艺术理念,并把前卫艺术和十月革命视为精神革命的统一体(尽管很天真),所以,他们必定被抛弃。而左翼木刻则放弃了原先只是同情大众的知识分子立场,最后成为革命大众的一员。从左翼的“艺术化大众”到延安的“大众化艺术”。从“艺术的道德至上”开始,终结于“道德(国家意识形态)至上的艺术”。左翼木刻因此逐步走向了“高调前卫”,从而颠覆了自己的初衷。宋江的故事在现代中国仍然在重复着。
而那个“中西合璧”现代性的实验在还远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被功能现实主义所代替。五十年代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就发展的充分和成熟性而言,似乎远远胜过中西合璧的中国现代艺术,但是它毕竟是苏联现实主义的派生物,并非是一种原创性的中国现代艺术体系。中国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早期元素,包括徐悲鸿的理想现实主义、以及后来董希文、王式廓、冯法祀等人的原生亲和的“土油画”写实传统实际上都在六十年代以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苏联学院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在文革期间达到高峰。所以,抗战之前的林、刘、庞等人的早期“中西合璧”的实验,甚至徐悲鸿的写意现实主义实际上都在五十年代以后中断了。我在1994年发表的《论毛泽东的大众艺术模式》一文中曾经分析和描述了这段历史。[13]
五四时期初的“中西合璧”现代性转移到台湾、香港和海外,并且和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对话,而在大陆,六十年代以后则彻底让位于群众运动形式的文化功能主义(文化革命)。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红卫兵运动确实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功能主义类似,但是二者的意识形态诉求则完全不同。
如果说,林风眠、刘海粟主要倾向于科学与玄学合璧的现代性,那么左翼木刻和徐悲鸿则是道德至上的现代性,最后还有一个以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陈师曾等为首的本土现代性。表面上看,这第三方面是反现代的,然而他们是典型的“中体西用”,以形神观对文人画进行现代性转化。这个口号即是“似与不似”之说。
早在清代,如石涛、恽寿平等人就曾提到“似与不似似之”的创作标准,这种说法又为黄宾虹、齐白石等人延承下来。如黄宾虹说“作画当以不似之似为真似”,齐白石也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说法。这种似与不似之间的说法应当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从传统美学的角度,它是魏晋时源起的形神观的延续。在唐宋艺术和文论中,魏晋的形神观逐渐变为写形与诗意的关系,其核心为“意境”之说。在元以后的文人画中又变为笔墨与性情的关系,其核心是“逸”。然而,文人画的最高境界,无论是笔墨还是性情,均不能走极端,而必须处于一种“中和之美”的境界。所以,“似与不似”是审美境界问题,不单单是视觉形象的似与不似的问题。
另一方面,清代石涛等人至黄宾虹、齐白石一再提“似与不似之间”的原则,都与西洋写实画风的舶来有关。这既是与写实画法抗衡的原则,同时又是在时风日转的景况下不得不稍参其法的措词。这种矛盾在现代中国画坛上较多地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齐白石、潘天寿等人的作品中显现出来了。因此,“美在似与不似之间”可以首先视为传统派的现代性策略。
无论是黄宾虹、潘天寿还是齐白石,均很注意写生。但是,这种写生不全都是策略使然。他们都很注重生活情趣。这给了他们一种观察的乐趣。在中国的理论中,“观察”不是模拟,而是师法造化。师法造化也是培养意趣品味。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是都表现了一种田园之趣,其中黄宾虹文人气息多一些。这种田园之趣固然与画家的出身和气质有关,但终归仍是他们的有意追求。齐白石衰年变法,有意摈除“冷逸”之调,以转“识者寡”的局面。潘天寿也向“篱落水边,幽花杂卉”中拾取诗情。因此,如果说他们在传统文人画的道路上有所发展的话,那就是将明清文人画中的“雅”变为“俗”,或者以“俗”为“雅”。然而,正是这些“俗”的情趣给他们的传统笔墨注入了一种现代性。扩充了明清文人画的偏于孤寂的自足情绪,使他们的绘画多少接近一些现实人的生活。他们的笔墨、题材和情趣都渗透着一种“家园”感觉。[14]在艺术日益接近西方,在艺术日益从属于社会而非艺术自身的时代,这些画家用传统维护着自己的家园。同时又不得不在自己并非擅长的“造形”再现的领域接受西方形式的挑战。所以,造形要求艺术家观察生活和事物的时候极端敏感和细致,这在海上画派任伯年、潘天寿的花草、齐白石的虾、丰子恺的漫画中都充分体现出来。生活和现代性不在于笔墨是否传统和现代,而在于对事物和环境的现代感受。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20世纪早期的现代性结构。如果我们把20世纪上半期不同的美术流派区分为以上三部分,[15]那么,林风眠、刘海粟等人的科学现代性主张以印象为方法表现人文情绪;徐悲鸿和左翼木刻运动的道德至上现代性则主张以写实方式象征性地表现理想社会和人格;而黄宾虹、齐白石和潘天寿的艺术本土性则以神形观(似与不似)或者传统写意为方法表达文人画的家园意境。这样,印象、象征和写意性就成为东方早期现代艺术的美学核心,而半“抽象”化的山水、传神的肖像则是这种早期东方现代艺术的主要形式和题材。 其中只有左翼木刻运动在道德至上方面走得最为极端,因此也成为日后革命大众艺术的先锋。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能同意那种“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的片面性导致了种现代文化产生断裂层”的说法。中国早期现代绘画在吸收外来成分时并非扔掉传统,相反,总是维护着旧有传统中某些因素。而不论是哪种途径,都最终走向一种矛盾契合——道德、形式、情趣的“和而不同”。这种共同点遂使现代画史上的三派最终殊途同归。在外在层面的写意、象征和印象的手法中互相共享某种“意象”特征。他们的现代性核心都是要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冲击之下寻找出路和建树自己的现代性特点。他们都找到了意和印象(林风眠)、意和象征(徐悲鸿)以及意和象形之间如何契合转化的特殊角度。
三个流派中,自1930年代中期以后,刘海粟、林风眠、赵无极这一派的“中西合璧”逐渐在大陆沦为边缘,成为非主流。但是他们的“传统写意+印象派”的形式和探索则成为一种“低调前卫”力量继续在台湾、香港和海外发展。这种东方意象的现代艺术却在五十年代台湾的“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运动中,以及六十年代的香港现代水墨和抽象绘画运动中的到复兴。所以,意象式的“中西合璧”在二十世纪往往表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是对当时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叛,另一方面他们还承负着改造和建设中国现代艺术体系的责任。尽管由于地缘政治和人文资源的局限,它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但是,他确实是中国20世纪艺术中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海外赵无极、朱德群等人的实践,不仅直接和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对话,同时还把中国美学散播到西方现代艺术之中。说它低调,是与左翼木刻运动的高调前卫相比,它的人文关怀似乎温和,它的作品似乎也没有任何社会叙事方面的挑战性,基本是意象风景或者半抽象的形式,说它前卫,是因为这种“中西合璧”的艺术从不屈服大众和权力,相反在台湾、香港和文革中的大陆往往成为挑战正统主流艺术甚至官方权威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的背景中,这种表面上似乎接近西方“艺术为艺术”的艺术,其存在本身就具有批判性和政治性。其知识分子性,甚至比标榜为革命大众先锋的艺术更为独立和更具有政治批判的意义。
一般来说,大陆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中西合璧”的现代艺术(岭南、上海、杭州等地)与台湾五十年代以“五月”和“东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运动,以及香港六十年代的现代艺术可以说是 一脉相承的。但是,它们所处的文化结构和面临的挑战对象是不同的。比如,大陆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面临的是西方现代的冲击和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东西方的未来和美学系统的融合革新是主要课题。如果上升到政治层次,它是新的民族国家问题的组成部分,东西方的合璧只是一个表面样式化的美学议题。但是,五十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虽然仍然以东西方整合为议题,但是,潜在的话语则是对国民党偏安的国家正统文化(以中国传统书画为代表)的反抗。国民党以正统文化标识台湾国民政府的正统国家地位,以有别于共产党政府的非正统的“伪(匪)”国家文化。“五月”和“东方”的出现正是对台湾五十年代的正统(传统)的保守主义的抵制,它们的东西方合璧的现代绘画是对现代同时也是对人性自由的表达。其动力部分来自对传统文人艺术的抵制。因为在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以后,国民党政政府将文人画和书法奉为国家正统的文化代表,这是失去政权的偏安政府的一种文化策略,也是一种政治心理的反映。在文化上显然是一种保守主义,所以台湾光复之后的艺术现代性就是从“五月”“东方”开始,其中“五月”多为水墨艺术,“东方”多为油画作品。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五月”“东方”的现代主义,在台湾很快被新兴的现代艺术运动所代替,一种达达、波普和禅宗乡土杂交的艺术运动出现,其超越的对象就是“五月”“东方”的早期现代。后者被认为太过于乌托邦,没有扎根在本土的现实之上。[16]
而香港的六十年代恰恰是现代主义发生发展的时期,以吕寿坤、王无邪、韩志勋、陈福善等人为先锋的现代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台湾的“五月”“东方”的触角延伸到欧美和香港。但是,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的潜在话语所抵制的既不是中国20世纪早期的西方现代,也不是台湾五十年代的国民党的国家正统文化,而是岭南画派的遗老文化,尽管岭南画派在20世纪初是现代水墨的新军,但是,到六十年代的香港年代已经沦为保守的唐人街文化的代表。所以,香港六十年代致力于中西合璧的艺术家的创作,不能脱离开这个复杂的大的历史上下文。从这个角度在去看韩志勋、王无邪、吕寿琨等人在六十年代的激情创作,就不会把它完全看作个人的情绪,它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先锋反叛意识。
上述五、六十年代在港台出现的“中西合璧”的“低调前卫”实际上在中国大陆也有,比如我在近年所作的《无名画会》历史的研究,证明了这种“低调前卫”作为某些局部现象,在六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之中是反抗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前卫姿态,当然,在那种环境中,它必须是一种低调“出世”的姿态。一般来说,它采取的形式是非宏大叙事的写生题材。
20世纪上半期的中西合璧的现代艺术(或者我们可以称其为低调前卫),必定被五十年代以后的正统、革命和国家意识的大众艺术边缘化。因为,首先,低调前卫是知识分子个人独立思想的产物;其次,它的理念是文化至上,是建立在长远的文化建树之上、而非政治实用基础上的;最后,因为它的艺术语言是精英的,不适合大众传媒,而低调前卫又不向流行时尚妥协,所以,必定被边缘化,甚至消失。这个早期的“中西合璧”的现代性,虽然符合长远的现代性建设,但是不得不终止。而以左翼木刻为代表的高调前卫,以道德至上和政治实用主义为价值取向,往往把文化和艺术作为服务工具。当道德至上和实用主义互为表里的时候,最初的理念、热情和信仰即会式微,甚至转化为自己最初对立的一面。始于高调,终于妥协。
三、 “理性绘画”与意派的关系
后文革艺术的分裂性
在20世纪末,中国艺术结束了国家意识形态一统的局面,文化革命之后又一次爆发了对现代性的追求,其面貌与20世纪早期的艺术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对“五四”时代的文化现代性的复兴尚需等到八十年代中期,因为“后文革”时代的艺术仍然是被文革扭曲的产物。或者说,它要么仍然是反文革的文革模式,比如伤痕。要么是绝对的纯艺术,比如抽象美、形式美。
伤痕和乡土的学院写实主义基本是悲怨。正如我在1985年发表的《近年油画发展的流派》一文中说,“(伤痕画家)用赤裸裸的现实,用直观的‘典型环境’暴露十年动乱,批判社会中的弊端。这是30年来的第一批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美术作品。但他们的批判还不是主要建基于理性的反思和彻悟之上,而是先前(文革)激情的逆向流泄,是对‘伤痕’的暴露,是对赤子情被亵渎的愤懑,是对痛苦和不幸的哀怨与控诉,是‘失去’的心理补偿。” [17]这些学院写实主义一方面表现了文革后的道德诉求,同时也配合了文革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传播,它的故事性和通俗易懂的写实手法成为最有效的言说形式。但是,这种现实暴露并非那种超越了自身(即所谓自身痛苦)的文化理性批判。所以,其现代诉求必然很快枯竭。更何况其形式和题材本来就很陈旧,于是很快堕入矫饰,并成为商业艺术的主要资源。
除了社会心理原因外,我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文革后这些写实艺术的两个表现方法的误区,一是缺乏传统“暗喻”的美学方法;二是根深蒂固的再现论。现实是一种深藏的结构,而非视觉表象。所以,反映现实必须超越直观现实,“表现社会变化所导致的文化结构的变化和时代心理特质,不是生活和物象的原型”。[18] 也就是以“意在言外“的方式把握现实的内在结构。
文革后艺术的第二个方面是学院唯美主义。它关注的是视觉形式的美感。[19] 虽然在文革之后,它也发挥了一种“人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功能,但是,它的纯艺术既没有艺术本体的批判性,也没有社会批判性。它在美学和形式方面所谓的“科学性”诉求也是纯粹形式的。正如我在《近年油画发展中的流派》中所说,“如果不是时时关注着形式构成关系是否与文化意象的谋合,而是关注形式构成本身就有唯美的倾向了。”[20]
“唯美主义”的代表是吴冠中先生的“形式美”和“抽象美”。然而,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三个事件集中体现了这个倾向,一个是1979年的北京首都机场壁画事件。新建的首都机场邀请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艺术家创作了一批壁画,由于这些画集中表现了这个时期“形式美”的追求,机场壁画大多强调技术性和形式美,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围绕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的少数民族妇女的裸体形象展开了争论。他触及到了文革时的道德禁区和形式禁区,这幅作品最后被铲掉。所以,袁运生不但成为当时“唯美主义”的代表,同时也成为追求形式美(人性)的英雄。[21]
“唯美主义”的第二个现象是一些沙龙式画会的出现,其中以“北京油画研究会”为代表。画会中的很多艺术家都曾经是文革美术的主要创作者之一。文革之后,准确地说,是从1978年开始,这些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才转而提倡非政治题材的、形式唯美的艺术。这种唯美主义的主要动力来自眼睛的视觉美感,基于此,他们转而完全排斥内容和任何与社会意识和情感倾向有关的“内容”。其口号是“个性”风格,不是人性的个体自由,只是个体的视觉美感。
第三个事件是关于“形式美”和“抽象美”的讨论。这个讨论在文革后就算是最激进的艺术现代性的美学诉求了。“唯美主义”的代言人是四十年代留学法国的吴冠中先生。吴冠中本人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参与革命美术的创作,相反致力于他的风景画创作。1980年,吴冠中在《美术》第十期发表了《关于抽象美》的文章,并立刻在美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吴的大致观点是,美是客观属性,是客体物质先天具有的,但是需要人从那些客体物质中发现并抽取出来,他说“要在客观物象中分析构成其美的因素,将这些形、色、虚实、节奏等等因素抽出来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这就是抽象美的探索。”[22]虽然,吴冠中说“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但是,似乎在他的文中,两者被看作一回事。而无论是抽象美还是形式美,其目的都是“美”。而他所谓的“抽”,也只是对视觉感觉的概括抽取。这和西方的“抽象主义”完全不一样,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中,人们会说abstract art(抽象艺术)或者abstraction (抽象主义) 以及formalism (形式主义)但是很少说abstract beauty(抽象美)或者 formalist beauty(形式美),因为,无论西方的抽象主义(abstraction)还是形式主义(formalism)都和“美”(beauty)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抽象和形式主义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概括视觉的美,而是反对旧的再现现实的语言和观念,反对模仿可视现实。但是,吴冠中认为,抽象美就是艺术家对视觉美感的表现。所以,吴冠中明确地反对西方抽象派,大概他认为后者不是美,而是丑。他还认为抽象美中国古已有之,比如,中国的园林、书法、古松以及八大山人和齐白石的画。在他看来,“似与不似”就是抽象美的核心。
表面上看,吴冠中的观点似乎和林风眠的类似,也是谈中西合璧,但不同的是,吴只是在形式上谈“抽象古已有之”,而林风眠则想把传统精神和西方现代形式合璧。吴冠中的观点表面上类似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就是形式”的命题,但实际上,吴的形式美命题没有精神乌托邦的依托,所以它是苍白、唯美和“无害”的。他的所谓中西合璧中没有“意”的成份和位置。
文革后艺术的第三个方面,是在野画会的出现,相对于学院写实和唯美,自发画会则更多地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自由声音,它与这个时期的诗歌运动以及摄影同属一个阵营。艺术在这些艺术家那里,更多地被视为个性自由的表现。艺术承担着社会功能,但是艺术本身的责任是表现自我。我在《近年油画发展的流派》一文中讨论了“星星画会”。并且第一次用“理性主义”概括他们的艺术活动。“理性主义”首先意味着破坏、怀疑和批判。[23] 进一步,那个时候我所说的“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是同义语,也就是说艺术首先应当承担社会道德理念。所以,“星星画会”以及在野的诗歌都具有很强的道德之上意识。但是,他们的艺术还没有被道德化。
与学院派纯艺术比较,在野的“纯艺术”或者“艺术为艺术”的口号是一个叛逆的理念,它建立在个性自由和社会民主的理念之上。正由于这些业余青年没有学院背景,所以,他们能够用一种在当时看来比较“新奇”的现代主义形式去表现这种自由理想。其实,这些现代形式在今天看来也是唯美和装饰的,但是,那里面渗透了生命的激情和冲动。它们也是浪漫主义的,因为现实是悲剧的不理想的。
这些在野的、沙龙式的聚会或者写生作画活动是文化革命期间出现的、在文革后的七十年代末发展为高峰。[24]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现代艺术的活动与文学诗歌和民主墙运动都是一个整体。1974年是北京的地下文艺活动最活跃的一年,画家和诗人们常常在一起聚会。文革后1979年轰动国内外的“星星美展”也是从这个1970年代的地下艺术运动中走出来的。而一些艺术家也常常把自己的画挂到民主墙去展示。[25]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北京共有五十余种非官方杂志出版。在这些杂志中,有属于文学性质的,如《今天》、《沃土》,大部分属于政治类的,如《探索》、《四五论坛》、《北京之春》。在这些刊物中,艺术家给诗人作插图则是常事。而在这些插图之中,业余的画家用抽象的形式美的方式表达对个人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渴望。它们远比学院的抽象绘画有灵魂。[26]
如果把七十年代的地下文艺看作中国文革后期开始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话,“个性”是它的核心与灵魂。个人风格和“自我表现”是主要追求。这种个人表现在北岛、顾城的朦胧诗和无名、星星的作品中常常表现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和自爱。要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在文革后期的出现恰恰是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和冷酷(也就是无人性)的一种叛逆。能够伤感多情,能够表达自我的困境和痛苦乃是一种人性复苏的征兆。在艺术中憧憬完美和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美学,这个美学由于太过于私人化,所以大多数艺术家都崇尚写意和印象派的中和,一种不成熟的“意象”形式。
所以,尽管七十年代的地下文艺的社会功能是对自由的呼唤,对封建集权的批判,但是,这种功能却是依附在小资产阶级美学趣味和“艺术为艺术”的美学观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星星”画会造成了政治事件,但是实际上,星星成员的作品,除了王克平的少数木雕具有政治意味之外,基本上都是风格化和“形式美”的、以抒情的居多。所以,七十年代的地下文艺,无论是在“星星”、“无名”以及朦胧诗的作品中,艺术家的美学观念和他们的社会意识似乎是以分裂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艺术的题材方面,是私人化的。但是在艺术观方面,是社会功能化的。事实上,正是这种个人化的艺术在社会功能上发挥了比学院写实的“伤痕”“乡土”那些表面政治化的题材更为先锋性的作用。[27]
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初的“低调前卫”又在文革后出现,不过这一次,艺术仍然低调,但是社会行为方面则是高调,特别是“星星画会”的游行。文革后的低调前卫是前卫,但是他们的“低调艺术”也还不成熟,同时也强迫自己把低调变高调,要它为政治服务。这就是分裂和不成熟,所以我把“无名”和“星星”等这个时期的沙龙社团艺术称之为“业余前卫”。事实上,这些艺术家本身也是业余的自学青年。
综上所述,在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段期间,中国艺术的现代化动力主要来自对文革艺术的逆反,就像20世纪初的美术革命主要针对传统文人画一样。但是,文革后的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和先锋主义实际上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文革模式规范着,是“反文革的文革”模式。它本身就是文革后处于激变之中的政治现实。它们的极端性导致一种强烈的二元对立,比如,政治/纯艺术、现实/抽象等,由此产生的分裂性是文革后艺术的特点。而这些问题,甚至在20上半期的美术革命中都不曾存在,在20世纪上半期,“五四”前后,艺术现代性的课题,包括艺术本体、道德美学和艺术科学性,通常是整一性地综合讨论的,尽管不同流派会有不同的倾向性。换句话说,道德、方法和艺术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典型的例子是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宗教说”。
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大众艺术则让艺术为政治服务,又回到了分离的二元论,要求艺术再现阶级斗争现实,虽然在广义的政治生活的层面上,毛泽东的大众艺术和生活得到了真正的融合,但是,艺术完全丧失了个人性,成为政治的婢女。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艺术、生活的整体性是中国二十世纪整一现代性的极端,因此也是对整一性现代性的颠覆。所以,“五四”并没有造成传统和现代的断裂,这种断裂的开始是在五十年代以后。后文革时代仍然延续着毛泽东时代的分裂话语,尽管题材和样式有了些许变化。承接“五四”的整一现代性的启蒙讨论,只有等到85运动出现才成为可能。
“理性绘画”:回归文化至上
严格讲,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85美术运动”在整体上都是“意派”。[28] 因为,文化至上的理想、结构中西的雄心和艺术、社会和人生整一地存在这三位一体的契合再次回归和复兴。其实,85运动的最重要之处不在于生产了多少好艺术家和好作品,而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现代性作为整体运动的核心价值被前卫艺术家所接受并且用不同方式去表达。艺术不再是艺术自身,85运动中不再有“艺术为艺术”;艺术不再是民族的,85运动的艺术家都讲超越东西方; 艺术也不再高喊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而是诉诸人文热情。正如, 我在《’85美术运动》一文中说,“1985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又一次文化变革运动。画坛上也出现了一场美术运动。它几乎包容了该年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问题,它是该年中西文化碰撞现象的组成部分。”[29]
85运动的特点是文化至上,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灵魂。如前所说,从“五四”时代开始,文化的概念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是超越了政治、科技和艺术分离性的现代性理念的载体。甚至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也含有文化整一性的意义,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一场政治运动却以“文化”命名。而书写、批判、大字报、样板戏等成为运动的主要手段。但是,文革毕竟还是政治运动。相反,五四运动和八十年代的文学艺术运动却都是以文化至上为宗旨的现代性诉求的高峰阶段。这种“文化之上”乃是“整一现代性” 的根本特点。从这个角度看,85运动超越了后文革时期各种“新艺术”的反文革的局限性,直接承接了世纪初的现代性启蒙运动。换句话说,它从直接的政治针对性进入了更为宽广的文化现代性,并且从美学、道德和社会的整体现代性角度审视艺术的发展,单纯用“图像学”去干预当下现实或者维护“艺术为艺术”都不再是85运动的直接目的。
由于文化至上的冲动,85运动摆脱了后文革艺术的政治/纯艺术的对立情结及其模式。而85运动的当紧目标是如何摆脱当时流行的悲怨写实再现(已经变为矫饰)和学院唯美主义,批判二者赖以成立的艺术再现的哲学基础。因为悲怨现实主义和唯美都出自其极端,无论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从这个角度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超越“会成为85运动的关键词之一,因为要摆脱反映现实的束缚是八十年代新艺术的唯一出路。
首先八十年代中期由学院毕业的这一代艺术家的经历已经和上一代知青艺术家的经历不同,他们对文革没有那么强烈的亲身经历,他们在文革是童年旁观者。此外他们经历了上一代所没有参与过的“文化热”,即八十年代中爆发的中西文化大讨论和出版热潮。加上他们对文革后艺术的反省,使他们的艺术视野更为广阔。艺术和文化重新回到了世纪初的启蒙和现代性层次,它对现代性的诉求,类似“五四”时期的人性启蒙运动。理性、反思和批判是85运动的关键词。
我本人是知青的一代,和后文革的伤痕以及无名、星星画家是一代人。但是我亲历了这一代和85一代两代人的意识经验。两代人都渴望个人意识的觉醒,但是表现形式不同。八十年代可能更抽象化。我曾经在《当代美术中的群体和个体意识》中谈到这一点。[30]但是,这个人意识不再是“自我表现”和“个性”。而是一种超越的理性。超越,在道德层面就是超政治主题,主张自由冥想;在科学美学的层面就是超越现实主义以及形式主义,因为它们都太感官和情绪化;在艺术本体层面就是融合艺术与非艺术的鸿沟。[31]
“超越”意识是理性的核心。然而,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无法从传统或者身边的中国哲学里找到那种超越和理性精神作为参照。所以,自然我们的目光转到了西方康德时代的(或者康德之前的莱布尼兹、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卡西尔)一些哲学家的哲学,比如,形而上学意志论(或者在马克思看来是唯心论)的倡导者——费希特的哲学。我曾经在《一个创作时代的终结》一文中引用过费希特这位德国18世纪的哲学家的一些话。那个时候当我读到他的《人的使命》一书时,真是激动!虽然,时代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是我看到了他的思想正是中国八十年代新一代所需要的。因为,费希特有关“超越具体和实用方可得到自由”的思想打动了我。费希特把意识分为自然体系和自由体系两类。他的自然体系不同于自然界的概念,而是缺少意志和理性的认识体系。而自由体系是由意志和理性所导引的意识体系,只有拥有这种理性意志,人才能获得自由。而自然体系否认了人的影响,只能冷漠地、死板地充当一面镜子,单纯反映各种变化着的事物,而根本无法积极干预事变的进程。
费希特的人的使命的哲学使我加强了对旧的现实反映论的批判力度。其实,当我在八十年代初写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我记得周围很多青年学者对之前流行的所谓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很反感。
那个时候,我们所要寻找的是一种脱开现实束缚的自我所意识到的自由精神。我们把它称之为“理性”。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回想那个时候的“理性”的时候,我感到,它和“意派”很接近,它是超越和整一,是不为任何现象(佛教所称之谓的实相)所迷惑的自由畅想!我们总是为现状所困扰,因为我们有一种观念误区。我们总把自己的精神与现状混在一起。看不到,我们为现实所做的一切努力,我们为现状所付出的责任,不是为了现状本身,而是为了建树一种超越的纯粹精神,这就是理性精神,只有得到这种精神境界,才能得到理想的未来。这种超越的理性才是自由的境界。 我在《一个创作时代的终结》那篇文章中批评了中国几十年艺术挥之不去的现实论,同时引用了费希特的一段话,我认为直到今天,它还有意义:
我看见,呵,我现在明显地看见我从前不留心或看不到精神事物的原因了。如果我们抱有满腔尘世目的,用种种想像与热忱忘怀于这些目的,仅仅为那实际上会在我们之外产生结果的概念所策动与驱使,为对于这种结果的渴求与爱好所策动与驱使,而对自行立法的,给我们树立纯粹精神目的的理性的真正推动作用却毫无感觉,冥顽不灵,那么,不朽的心灵就会依然被固定在土地上,被束缚住自己的羽翼,我们的哲学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与生命的历史,并且像我们寻找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也思考整个的人及其使命。如果只为渴求这个世界上实际可能产生的东西所驱使,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32]
这种超越和纯粹精神的自由才是我在1985年在每篇文章中都多次提出“理性”的根本原因。要超越现实,就必须进入一种纯粹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有点儿类似宗教的那种对现实的超越性和崇高感。我们所说的自由,不论是个人的还是人类的,都必须建立在这种理性之上,否则,就会被政治的、物质的现状所困扰。如果有了这种理性,我们对现状的判断就是坦然的了。因为,我们为之热情投入的现状不过是一个通向未来自由的一个点,它永远是不理想的。我们的投入因此就不是为了现状,而是为了理想的自由。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对现状作出根本性的判断,才能超越琐碎现实,从而以意志去干预和引导它。归根结底,自由的敌人不是现状的某些表象,而是人自身的非理性。
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看来,非理性就是对现状的屈服、服从,那怕是对现实痛苦的再现或者模仿表现,都是对现实的屈服。其形式必定是感性的和自我情绪化的。其表象形态上的“自由”,反映了意识的不自由。所以,我对明清文人画的自娱,对明清文人的那种偏于道德和个人趣味的自我完善不屑一顾,因为它缺少超越和形而上的动力,相反对北宋的理学及其影响之下的宏伟山水则很崇拜。在当时的所有文章中,对文革后艺术的自我风格表现和模仿现实的矫饰风,都很排斥。[33] 总之,对个人理性意志的提倡是我在那个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批评基点,之所以极端投入地倡导这种似乎“唯心”的哲学,首先出自我对中国当代艺术始终陷入为现实所俘虏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大量阅读了布莱希特、康德、费希特、卡西尔等人的著作,从中所受到启发,和自己的批判观念不谋而合。后来当我的批判立场遇到了北方群体、江苏的杨志麟、丁方、徐累(后来的红色旅),以及上海的建军、李山和浙江张培力、耿建翌等人的艺术实践和观点时,非常激动,并把他们视为同道。同时,我和云南的毛旭辉以及85群体的艺术家通信,一起畅谈这种超越的精神哲学。
在1986年所写的《理性绘画》一文,是这个时期我对“超越”和“理性”的思考总结,并且以许多群体的艺术理念和作品为例进行了阐发。文中,我首先对“理性”作了解释。理性包括三点。
(一)、首先理性精神是一种超越琐碎现实的永恒秩序,它和真理相通。“但是,这里的“真理”(理性)不是某种实际经验的概括总结,而是一种超验的、带有构筑意志的、具有永恒原则或崇高精神的对世界秩序的表达。” [34]
(二)、 其次,理性是反思。但是,反思必须建立在“理性的真理”之上,而不是“事实的真理”之上。 ‘事实的真理’很可能是偶然的,而只有‘理性的真理’是必然的。 [35]
(三)、理性是自我意志和自由。“对自我意识的赞颂是对人类自由的追求,有了自由意志,人才能成为理性的存在。但是这种自由意志又必然要回归到历史与人类的长河中去。这种主观意志的自由即是‘人应当用人类去解释,而不是人类应当用人去解释’”换句话说,“人”是意志和自由的载体,不是充斥感觉和个性的偶然性个体。[36]
很明显,这个时期对人性意识的理解已经不同于后文革时期的各种流派,无论是伤痕乡土的悲怨派,学院的个性唯美派,还是业余前卫的个人表现派,在我看来都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其人的觉醒意识是“当下自由”,而不是“永恒自由”。后者是一种尊严,高贵人性的尊严,而不是一种乞丐的自由。但是,这种尊严在今天充斥着操作和利益关系的文化和艺术世界中,到底还有多少价值? 甚至往日那些理性的追求者都已经在唾弃着理性。理性不是一种不着边际的价值理想,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自在、自为、自由的精神!它不为任何“实相”所驱动。
总结起来,在我的《理性绘画》一文中,我定义的理性,是超越现实的意识;它是对真理而非事实的判断;是人性的自由,但这里的人首先不是个人的,而是人类的,不是当下的感性的,而是长久自在的。概而言之,理性绘画就是反直观化、反局部化和反个人化的艺术哲学。 而所有这些都和85美术运动的反现实再现的基本哲学有关。
理性“反思”和“超越”几乎是85运动中大多数艺术家的共性,正如我在《理性绘画》中所说:“就这种理性精神的追求和反思特点而言,目前大多数青年画家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所具备。即令是崇尚直觉的许多作品中也反映着创作主体所执意要表现的某种生命哲理、人生轨迹或者感悟到的‘宇宙的秩序’。直觉——无论是意念直觉、性灵直觉或情趣直觉中的先发性的顿悟与理性绘画的先发性的思考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37]这里所说的崇尚直觉的主要指毛旭辉、张晓刚和叶永青等人艺术中的“原始生命秩序”,我把它称之为“生命之流”。他们的自然意识较之以前“乡土绘画”的自然再现是一种超越,试图将人性回归宇宙和大自然,而不仅仅是欣赏某些人的淳朴无华的视觉经验。
所以,85时期的绘画,特别是在“理性绘画”中,人物形象大都是背部,没有五官特点,因为他们不是个人,而是人类;背景大多是空的,因为它们不是再现一个具体的当下的场景,而是一个宇宙时空;构图中的人和人、人和景、人和物都不是处于一个叙事的逻辑之中,这里没有情节和对话,因为这是一种人的冥想,是人和物,人和情境的契合对悟。所以,人、物、场都处于一个在通常再现的构图中所不存在的图景中,也就是“人非人、物非物、场非场”的似是而非的图像结构。然而从意识的自由,理性的自在的角度,把这些“不是”放到一起,就都成为一种特定的言外之意的模式。不论是人、景物还是所谓的方、圆、线、点等等符号都被一视同仁地视为有理性的万物。那些在西方抽象主义看来是几何逻辑的物质形状的点、线、面,在理性绘画那里是有生命的,可以言说的意识载体,而非物理的分割边界。
如果我们回到最初我们所讨论的中国“整一现代性”的文化特点的话,理性绘画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对现实道德、政治和艺术之间的支离性和琐碎性的静观把握。通过感悟式的悟对整体性地把握世界,把握人、事物和情境的契合(或者错位)的关系。这就是对世界的“文化化”(culturalization)理解,文化是智慧,是冥想,是静观。不是被困惑、痛苦或者欲望所干扰的模仿和追随。而模仿和追随正是是分离和再现的哲学基础,因为它试图把文化视为对某种现实认识的替代物。所以,本来处于整体状态的文化(精神)被支离为所谓的各种表现风格(写实的、抽象的或者表现的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经验感觉的代名词。正如前面所说,经验感觉表现的是“事实的真理”,而不是“自由的真理”。“事实的真理”是出于支离逻辑之中的“真实”, “自由的真理”则是面对整体世界关系的“自在”。所谓的“真实”其实并不存在,因为通常所说的“真实”不过是一种支离表象,而自由则是那个能够把握世界关系(人、物、场,或者理、识、形的关系)的自在意识。
简而言之,“理性绘画”就是用绘画之中的“似与不似”和“不是之是”的关系(人、物和场的虚构关系)去表现某种意识原理的艺术。
但是,理性绘画并没有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就被放弃了。85美术运动的整一性现代性意识也走向式微。1988年,在经济大潮和政治危机的冲击之下,从1985至1987年期间那种“文化至上”的前卫群体实践开始消解。85运动的少数画家提出了“消解人文热情”的口号。其出发点可能是反省85运动中存在的虚泛宏大的崇高叙事,这是其批判的积极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清理人文热情” 的口号没有看到理性绘画的核心其实不是宏大叙事的题材本身(尽管在一些艺术家那里,有这种倾向),而是反再现和超越现实经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年,在85运动中,同时还出现了追求学院纯化语言的倾向,与其相对,出现了提倡艺术重新回归政治现实的“大灵魂”的口号。这两种倾向,都试图转移85运动的文化至上的实践,回到政治/艺术二元对立的老路。在八十年代社会处于整体骚动的年代,政治改革遇到瓶颈、经济生态亟待整顿的时刻,文化实用主义再次成为主导动力,浅尝辄止也随之再次出现。
在理性绘画和生命之流之外,85运动中那些受到了西方观念艺术影响的“行为观念”艺术,实际上也表现了一种有别于西方观念艺术的文化整一性观念。从当代艺术史的层次上,85运动的“观念艺术”从“反艺术”的角度对后文革艺术进行了反思、批判和超越。比如,不少85运动的艺术家对“个人”风格和“自我表现”的批判。从艺术本体的层次上,无论是“厦门达达”、上海“M群体”等倾向于哲学思考的观念艺术,还是吴山专、徐冰、谷文达等用中文为媒介的观念艺术,或者以行为艺术和文化活动为主的观念艺术,基本都想从根本上彻底打破艺术再现生活的旧观念,艺术和生活本来就是一体的。
然而,他们所主张的艺术和生活的整一性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那种在美学自身寻找艺术与生活融合的观念,相反试图干预社会行为。一些乡村活动、展览冲突,被封闭等等,实际上不完全都是有关中国政治生态的问题,它们和艺术家的这种观念意识分不开。当九十年代全球化、市场和都市化来到以后,类似行为照样大量出现在街头艺术之中。比如,王晋在1996年所做的冰墙《96中原》。
所以,中国的所谓的“观念艺术”在本质上是反观念的。我曾经在1998年发表的英文文章《反观念的“观念艺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当代艺术》(一文中,讨论分析了这个特点。[38]比如,禅宗的劈竹、挑水都是佛的观念被黄永砯运用到他的艺术中。他的《灰尘系列》,把画布放在做饭的炉子旁,让烟熏火燎的环境留在画布上“作画”;上美术课的小学生削铅笔时把铅笔屑留在画布上,其痕迹自然成为反绘画的“抽象”绘画,等等。这里的核心是艺术和生活的一体化。
无论是这个时期的绘画、观念艺术甚至行为艺术都和文化的生态性和仪式性有关。仪式性和生态性隐含着过程、自然和参与的意念。所以,它鲜活生动,与存在、生活、世界一体。85美术运动是五四时期之后的第二次在整体上具有“文化至上”的现代性意识的运动。但是,就像五四时期一样,它同样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不应当抱怨外部环境和历史的干预,也不应当将责任归于某些同道的放弃,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集体的角度——从85运动参与者的整体角度,甚至从所有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角度,都应当深刻反省我们自己,反省我们的责任感和意志力。没有这个反省,我们仍然会重复浅尝辄止的苦果。
四、 在体制与市场共谋的时代,只有“玄想”可以为艺术提供自由空间
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在进入90年代以后面临20世纪以来最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在精神层面,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严重失落。事实上,文化界的精神拐点并非完全是以1989年“六四”事件为转折,早在1987和1988年,从理想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转折已经出现。这种对艺术中表现“人文热情”的放弃实际上并不是对某种所谓理性绘画的“玄学”体裁的抛弃,而是对理性主义的放弃。这种放弃在现实中可能是“合理”的。因为艺术家必须面对日益高涨的经济压力和市场的魅力。确实,现实并非纯净的真空,腐败和政治改革等政治气氛的巨大冲击,都是“艺术回归现实”的正当理由。但是,这个理由的充分性和建树艺术体系的合理性是两回事。20世纪历史告诉我们,凡是艺术紧贴现实的时候,就是艺术被实用主义俘虏的时候。
所以,八十年代后期,从现实实用的角度,一些“理性绘画”的画家放弃人文热情似乎没有错,它是一种艺术再现现实和道德至上诉求的回归。艺术家追求道德诉求是对的,但是道德和艺术家的生活、世界应该是一体的,不可分裂。九十年代初的政治环境迫使艺术家重拾社会政治叙事模式,不过改换了文革图像学的宏伟模式,一变而为反讽模式,以达到对威权的颠覆性效果。但是,这种初衷很快被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市场利益所同化。高调的“艺术道德化”又一次跌入“道德化的艺术”的老路。
艺术重新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为政治服务的起点,只不过现在是另一种政治,一种对内部政治的犬儒主义和对外部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半推半就的姿态,从此中国开始了一种圆滑主义的政治学叙事。这种叙事甚至在中国20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可以说,它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私生子,是冷战时期向全球化市场时期转折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叙事,是在1992年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在俄亥俄大学看到了一个前苏联的展览,展出了一些中国政治波普的“前辈”、前苏联1970年代的Sots Art的作品。这些艺术家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图像与美国波普拼凑,创作了苏联波普艺术。那个时候我在出国之前已经看到了一些人的波普作品。当看到苏联的波普后,很吃惊。又进一步从大学的东欧专家那里了解到,这些苏联艺术家都获得了美国机构的支持,市场也很火爆。而缘起则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所罗门对这些艺术的长篇报道。所罗门在1993年又如法炮制,在《纽约时报》的一期周刊对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前卫艺术进行了长篇高调报道,并认为在冷战后这些作品中的扭曲“大脸”的“怒吼”可以拯救中国。显然,所罗门把这类政治叙事的作品视为高调的意识形态的产物。事实上,一些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也这种高调前卫的姿态向西方输出自己的作品。由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早期市场主要是西方记者、使馆和画廊操作的,所以,这些高调前卫即成为西方美术馆和市场主要追逐的样板。与苏联艺术家在苏联倒塌后也就无人问津的命运不同,中国的高调前卫赶上了全球化和中国国力的崛起。
在21世纪初,当这种圆滑主义的政治学叙事在全球市场扩展和中国崛起的形势下逐渐失效之后,转而投向新的“政治正确”性,甚至取悦于国家政治变体后的民族主义。其圆滑策略永远在调整之中。我在1995年发表的《权力、媚俗与共犯:政治波普现象分析》一文中讨论了这种圆滑主义在冷战意识形态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左右逢源的立场。[39] 实际上,我在1993年为《中国艺术家四人展》所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大事记》中以及那个时候所写的英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这种新前卫的机会主义特点。[40]
这种政治学叙事实际上再次把前卫艺术从八十年代所致力的艺术与生活、美学与社会的融合整一,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图像学传统之中。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艺术毕竟还在宣称一种理想,宣称艺术与生活的同一性和替代性。而九十年代以来的圆滑政治叙事则试图回避这种意义对应。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叙事往往与作者那不断变化的“政治正确”的立场相对应。“政治正确”于是在某些上下文中就变得异常复杂,往往和政治体制、市场、国外政治利益发生多重的共谋关系。这里的“共谋”概念并不是说有意识的共同合作和筹谋,而是指某种心领神会的非直接接触的配合。它不是政治行政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学概念。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种“共谋”只扣在某个艺术风格或者类型上是不公平的。因为,今天这种圆滑主义和共谋性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图像志”之中到处可见。不仅限于政治叙事,在时尚、传统和民俗叙事中也存在。可以说,任何人已经无法逃脱这种圆滑主义的诱惑,否则,你无法成功。
今日中国已经进入全面体制的时代,说它全面是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而言。中国的体制是政治体制和资本体制共存共谋的特殊系统,其体制优势是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而中国当代艺术已经不得不成为这种体制的附属品,所以它也正在享受着这种共处的优势。今天,有些人相信资本可以带给艺术家自由,其实那是有限的。为市场价值而重复和放纵的背后,是艺术家正在逐渐失去的自由,即想象力的枯竭。今天,20世纪初所憧憬的科学以及工具理性都越来越与全球化、都市化进程相匹配。波德莱尔时代所描述的中产阶级的庸俗、麻木和铜臭气充斥在中国当代文化之中。艺术除了模仿时尚之外,越来越没有想象力。知识分子的洞见、智慧和信仰很难见到。因为,在以往的国家意识形态和集体信仰消失之后,拜金和时尚很快填充了前者留下的想象的空白。再也没有纯粹精神那么回事。如果有,也是私密的、个人的事。精神和信仰只能在家里、在私人空间中找到归宿。
这不得不迫使我们对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革命、断裂、进步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科学、工具理性、时间和金钱可换算性等等给人类世界带来了什么?现代的断裂性不但给人类带来了民主和科技。在人造物质日益丰富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科学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理性的成果,同时也是征服自然和满足人类私有财产和权利占有欲的毁灭性手段。阿德诺把现代“工具理性”看作人性占有欲在科学时代的集中体现。今日中国已经把西方的工具理性和自身先天具有的实用主义完美结合在一起,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然和外部世界完全被视为征服对象。现代性发明的这种世界关系方面的对立和紧张构成了现代艺术的断裂和分离,按照比格尔的说法,前卫的起源就是抵制市场体制;因此美学独立就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立场;而在方法论上,就是形式与精神的极端分裂和对立性。这一切都出自现代性对人与世界的契合关系的破坏。
然而,我们还在运用全部的国家资源在这个现代性快车上急驶,除了社会体制之外,迄今为止,西方所有工业、都市现代化的方案,我们照单全收,实施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艺术上,则极力推行文化产业这个在西方一百多年来已经被知识分子批判了好几轮的文化机制。在艺术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核心——替代和再现的哲学基础没有丝毫的批判,相反仍然在模仿和追随。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出意派论的根本出发点。意派的终极目的不是艺术产品,而是世界关系和人性契合的回归。
我们还能再次回到传统文化所崇尚的人、物、场互动契合,人类与自然和谐、而非分离对立的生态以及精神境界吗?我们为什么要丢掉这种境界、这种心态乃至认识世界的方式呢?
今天,如果科技、工具理性和族群对抗已经无法企及我们的自由和理想的境界,那么唯一能够摆脱掉这些不理想现实束缚的就是“玄想”了。这里的“玄学”冥想不是东方神秘主义,而是在艺术中贮存一种寄托,想像一种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境界,让现实中处于忙乱的心绪有个归宿,让不理想的现实变得“理想”。这可能就是真正意义的自由。获取自由和独立,首先要建立能够想象和建树这个自由的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我之所以看到公寓艺术和极多主义(以及类似的艺术家及其艺术)的难得之处,并不在于这些艺术作品本身有多么了不起。而在于这些艺术家试图寻找这种自由的东西。他们可能没有那么伟大,也不高调,更不是明星材料。他们以自我充实的过程无言抵制一个不可抵制的体制空间。
艺术在其中充当了艺术家与物和境发生关系的媒介角色。因此,我们评判艺术的标准不再是所谓的作品风格的完善或者独创性,而是自我充实过程的独特方式。自我充实是一种空间,不再是一种物质表面的形式构图,或者图像构成。所以,我在《中国极多主义》那本书中分析了极多主义与早期西方现代主义以及晚期现代,或者后现代之间的区别。
而早在九十年代中,为策划Inside Out做考察时,我就在大陆以及台湾和香港发现了这种极多主义的现象,只是那时无暇举办专题展览,只是在1998年在纽约开幕的Inside Out展览中纳入了台湾艺术家庄普、陈慧娇、朱嘉华等人类似极多主义的作品。后来,在2001年纽约中国现代艺术研究会主办的一个中国画研讨会上我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画中的极多主义”演讲,并且在《墙》展中,把极多主义作为一个部分。我在2003年分别在北京和纽约举办了《中国极多主义》的展览。[41]
极多主义和公寓艺术属于同一类主要以私密空间(一般是家)为活动基地的自我充实的艺术。我在1998年发表的英文文章《从精英到小人物:大陆前卫艺术的转折阶段》(From Elite to Small Man: The Many Faces of a Transitional Avant-Garde in Mainland China)首次提到“公寓艺术”,并分析了这种艺术的不可卖、不可展的特点,以及面对外部压制,国际市场和展览的忽视以及缺少公众注意力等困难。艺术家以自我放逐保持自我精神的完整和充实来无言对抗和抵制外部环境的创作和冥想,[42]宋冬、王晋、朱金石、王鲁炎、耿建翌等一批艺术家参与。极多主义和公寓艺术也很难分开。简朴、日常、重复、面对自己等都和传统禅宗的形式理念相关,尽管艺术家未必想到禅宗。这是一种特殊时代特殊产生的“都市禅”。[43]
“都市禅”不是指艺术家真的在坐禅,也不是出家。是艺术家的精神、生活以及艺术创作的整一性存在。它是一种能够保持独立个人精神的都市“第三空间”,是低调的文化责任和自我完善精神的归宿。今天,当看到了太多的哗众取宠的巨型艺术,这些无论资本和社会主义都需要的“媚力”之后, 人们希望看到一些实在的、渺小低调的东西。艺术与人、与作品中所说的东西应该是一回事。
从文化至上的角度比较,八十年代理性绘画的“超越”在九十年代并没有结束。只是从文化的教化回到了自我放逐。其实,理性绘画的“宏大”和极多主义以及公寓艺术的“渺小”在超越现实的层面上是一致的。任戬《元化》和宋冬的水写《日记》,就精神性而言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意在追索某种无限性,一个试图在可见的长卷中呈现它,另一个努力在不可见的每日过程中体验它。它们都是玄想的,但又是实在的,属于自己的。
五、 结 论 :“文化至上、结构中西、整一存在”三位一体的低调前卫
如果我们从中国艺术百年来的现代性历史的角度界定“整一性”和“意派”的话,是否可以说它就是那个最早在“五四”时期出现的“文化至上、结构中西、整一存在”的三位一体的低调前卫?有人会说,有谁不是在做文化?谁不是中西合璧?谁不是与社会同在?问得有理。然而,这里说的三位一体是主动性的选择和存在。是跨越时间的长期坚持,不是浅尝辄止后急功近利。
“文化至上”即是把文化系统的建设视为艺术的根本,文化在中国历史情境中是一种包容了政治立场、宗教倾向和行为实践标准的整一性概念,它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那种与宗教、政治分离的文化概念。因此,意派拒绝任何政治至上、艺术至上或者宗教至上的极端分离和独立的艺术观,相反主张文化至上的整一和契合。
“结构中西”是现代和当代中国情境中所必需的特定的创造性和方法论,不是表面的中西形式、中西表象的组合拼凑。它呈现了建树体系的雄心。
艺术生活的“整一存在”。不是艺术为社会生活服务或者让作品反映生活,而是艺术的创作与艺术家的生活状态以及艺术家对周遭社会空间的态度的契合。传统“画如其人”有这个意思,但是,“画如其人”更多地是从风格和品味的角度判断人的品质。当代的整一性是指艺术家的立场、其作品制作以及周遭情境之间的自然默契。也就是人、物、场的的自然关系。
“低调前卫”就是不主要依赖宣言或者作品图像或者题材叙事去宣示自己的前卫性,而是用思考、日常行为以及作品所有因素的整体性存在宣示其前卫性。不是言说,而是存在本身就是前卫。前卫的激进品质不只是体现在一种分离的姿态和极端性,相反它是一种独立性,独立于任何形式的权威话语(不论是政治的还是商业的),但是同时承认共存共生的知识分子立场、行为和文化生产。
通常,低调和前卫可能是一对矛盾。低调如何前卫?但它正是中国复杂社会结构的产物。西方的前卫,不存在高调和低调之分,因为西方的前卫本质就是和社会疏离,它本身就是在美学极端当中去追求反传统、断裂和革命等等,它不跟社会发生直接关系,所以,它既是高调也是低调。由于中国从延安时代开始就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和社会的直接关系导致艺术的现代性立场及其语言永远摆脱不了高调和低调之分。高调前卫意在当下和现实性,低调意在未来和长远。所以,高调前卫常常最终自我颠覆,低调者则有时不得不自我放逐。高调前卫追求语言的通俗易懂、大众化和时尚化,低调则坚持超越现实、非通俗性和体系的建树。
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中,高调前卫和低调前卫曾经是共生的,尽管并非平衡发展。低调和高调也会互相转化。比如理性绘画向政治波普的转化。但是,21世纪尽管文化冲突仍然不断,然而这个时代将检验非西方文化是否可以象西方现代主义那样为建树人类艺术和文明做出有智慧的奉献,而不是象在20世纪那样,仅仅或者更多地关注如何解决自己族群的当下现实问题。于是,低调和高调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或者干脆不复存在。
2009年8月初稿,2009年10月修改定稿
1 胡适,《实验主义》,载《新青年》六卷四号,1921年。
2 在艺术和文化上首先提出中西合璧的是康、梁。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首先起而否定明清文人画,出于救国自强之心,他大声疾呼:“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国人岂无英绝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见康有为,《万目草堂藏画目》)。另一位戊戌变法的志士,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也在其《欧洲心影录》一书之中批判明清绘画,推崇宋画,并认为中西合璧乃是中国艺术之前途,是新时代、新文化的开始。
3 关于中国现代性和现代艺术的描述和讨论,参见高名潞《整一性:中国现代性的逻辑》,发表在宋晓霞主编《“自觉”与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326-346页
4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1916年2月
5 如鲁迅所说:“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丛之以转移。”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七),《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6 林风眠,《东西艺术之前途》,1926年,《艺术丛论》,《林风眠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7 刘海粟,《西湖风景题跋》,1925年。
8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绘学杂志》,蔡元培主编,1920年6月
9 同上
10 李松,《徐悲鸿年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11 同上。
12 我曾经在《中国画的历史与未来》一文中论述了这个现代艺术史上的殊途同归现象。《走向未来》杂志,1985年创刊号。
13 高名潞《论毛泽东的大众艺术模式》,载《21世纪》,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第四期, 61 – 73页.
14 关于文人传统派的“家园”(home)概念,这是纽约大学的艺术史教授Jonathan Hay 提出的概念。那是他在1995年的《中国现代艺术》的一个讲座中首次提到的。给我印象至深。讲座原文尚未发表,这里引用时特别向Hay 教授致以谢意。
15 中国早期艺术的现代性是多重的。大体应该分为观念上的艺术革命;西方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都市市民文化的出现;最后是所谓的精英艺术家群的创造。这里的意派和现代性课题,主要集中在精英艺术家群方面。
16 关于台湾六十年代的“复合”艺术与“五月”“东方”的关系,参见拙作”Conceptual Art with Anticonceptual Attitude: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in Global Conceptualism: Points of Origin, 1950s – 1980s, Queens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9,127 – 139, 《反观念的“观念艺术”:大陆、台湾、香港的当代艺术》发表在《全球观念主义缘起——1950年代至1980年代》,纽约皇后美术馆,1999年。127 – 139 页。关于台湾复合艺术的详细介绍,参见赖瑛瑛著《六十年代台湾复合艺术研究》,台湾国泰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
17 高名潞,《近年油画发展的流派》,《美术》1985年第7期,第62-65页。
18 同上。
19 同上,我在文中说:“与‘伤痕流’几乎同时,出于对一元式的规范的形式手法的厌恶,唯美的画风也问世了。画家萌生了久久压在心底的对于‘美’的追求。他们要冲破禁欲主义的禁锢。
20 同上。
21 我在《近年油画发展中的流派》一文中(《美术》1985年第7期,第62-65页)谈到文革后的唯美倾向。我谈到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时说,他“追求人体‘美’、色彩‘美’、线条‘美’、组织‘美’。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最令人兴奋的是奇妙的西双版纳和傣族人民的美。’‘这是一个既丰富而又单纯的线条世界——柔和而富有弹性的线条、挺拔秀丽的线条,也有挚着、缠绵、缓慢游丝一般的线条。” (袁运生,《壁画之梦》,《美术研究》1980年1期)”。
22 吴冠中:《关于抽象美》,《美术》1980年第10期,第38页。
23 我在《近年油画发展的流派》一文中把“星星画会”列为“理性主义”。我说“在任何一个伟大的情感复兴之前,必须有一场理性的破坏运动。这个破坏运动出现了。由青年业余画家和专业画家组成的一些画会,特别是‘星星画会’,为这一运动的先锋派。艺术要介入社会,要抹去阴影,歌颂光明。真是热血青年!而他们的艺术观也可以说是功能主义,在这一观念支配下,他们要破坏旧的形式观念。” (《美术》1985年第7期,第63页)。
24 见高名潞主编:《“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就是1970年代的地下文艺运动。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都有一批艺术青年,他们藐视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艺术,向往现代主义。他们大多是自学的知识青年,在文革中没有正常教育的情况下,他们大量阅读中国古典,特别是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他们自学绘画,以印象派、后期印象派为参考。比如,1973年至1979年,在北京,有一个“玉渊潭”画派,也就是“无名画会”的前身。
25 1978年8月,文革后复刊的首期《中国青年》杂志由于刊登“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参与者的文章被禁。《中国青年》编辑部将该期杂志贴在北京西单的一面墙上以示抗议。自此,此面墙壁成为大字报的汇集之地,被称为"民主墙"。开始,"民主墙"上大字报的内容更多涉及文革冤假错案,渐渐发展到反思毛泽东及其思想并公开要求民主、人权、法治、言论自由。
26 事实上,北京七十年代的地下艺术可以分成三个松散的圈子。一个是“玉渊画派”,也就是“无名画会”的前身,这一圈子主张彻底脱离政治的“艺术为艺术”;第二个圈子是“星星”,虽然他们的艺术形式也是“艺术为艺术”,但是他们主张艺术干预社会;第三个是以关伟、关乃忻、宋红、龙念南等人为主的圈子,是一个似乎介于无名和星星之间的绘画圈子,这个圈子虽然也主张“艺术为艺术”,但是认为它应该是艺术行为本身,或者人生的一部分。艺术既不是艺术本身(像无名那样),也不应该把艺术当作政治工具(就像“星星”那样),艺术应当是人生的一部分,是日常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艺术观更像是艺术的人生态度。所以,我觉得应当把这个圈子称之为隐逸态度的“逍遥派”。有关这些艺术家的活动,见《中国公寓艺术系列之一:后文革的艺术生态》,水木艺术空间,2008年。
27 在八十年代初,抽象美作为纯艺术的追求,却导致了政治的先锋性。顾德新、王鲁炎等多次在小西天新明胡同和团结湖的张伟家举办半公开的小型展览。“星星画会”的主要成员黄锐、马德升、严力等和诗人芒克、毛头等均到场参观。1985年9月张伟等在北京朝阳剧场组织了一届抽象艺术展,但是被官方封闭。在上海,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有李山、余友涵等人在八十年代初多次组织“抽象”类型的展览,比如“凹凸展”等,同样引起很大的争议。而上海的“草草画会”和重庆的“野草画会”同样引起争议,“野草”被关闭。在西安,1981年《西安现代艺术展》也同样遭到了官方的关闭,甚至其中的一位艺术家还被判处了死刑,执行枪决。
28 八十年代中,大约近一百个自发组织的艺术在全国各地出现,从1985年到1989年被称为'85美术运动时期。见高名潞《’85美术运动》,《美术家通讯》1986年第5期。 有近期出版两卷本《85美术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9 高名潞《’85美术运动》,《美术家通讯》1986年第5期。
30 高名潞《当代美术中的群体和个体意识》,载《中国美术报》1985年第x 期,第一版。
31 我在1985年所发表的所有文章里,包括《当代美术中的群体和个体意识》、《三个层次的比较》、《一个创作时代 的终结》和《新洋务与新国粹》等都把这种理性和个人意识视为最关键的动因,并且结合青年艺术家的思想和作品讨论,同时批评后文革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庸俗现实主义。
32 费希特,《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7-118 页。我在《一个创作时代的终结》一文中引用了这段话,见《美术思潮》1986年第一期。
33 我在1985年在《走向未来》杂志发表的《中国画的历史与未来》一文丛理性的角度对明清文人画进行了批判。我在文中对传统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从北宋的理性和崇高走向明清的个人表现(所谓的自我完善)进行了批判。
34 高名潞,《理性绘画》,《美术》1986年第8期,第41-47 页。
35 同上,第 41页。我在文中说,“这反思又有双重层次,即对社会与人生的审视和对整个文化传统及其制约着的道德价值、宇宙观等形而上的问题的思考和探究。这种反思的过程是由‘器’入‘道’,由经验到演绎,由感情到理智的过程。实际上,这种反思在新时期开始就已出现,如批判现实主义的‘伤痕流’绘画和乡土自然主义的‘生活流绘画’是对‘十年’的反思,知青画家是其主将,因而人们说他们是‘思考的一代’,但是他们对真理的重新追求和对逝去的历史的反思是基于经验之上的,特别是情感经验之上的,他们追索的真理,按莱布尼茨所说应是‘事实的真理’,‘事实的真理’很可能是偶然的,而只有‘理性的真理’是必然的。”
36 同上。
37 同上。
38 见高名潞:“Conceptual Art with Anti-conceptual Attitude” in Global Conceptualism: the Point of
Origin 1950s-1980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pp.127-139. 该发表物是我和来自全球9位策划人共同策划的一个称之为《原点:全球观念主义 ——1950年代至1980年代》展览的图录。
39 高名潞《权力、媚俗与共犯:政治波普现象分析》,《雄狮美术》总 297期, (1995年11月
号)第36–57页。
40 "Chronology of Chinese Avant-Garde Art, 1979-1993," in the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Fragmented Memory: The Chinese Avant-Garde in Exile, The Wexner Center for Arts, 1993, pp. 14
– 19 . 同样,在另一篇英文文章中也写道这种机会主义。“The Avant-Garde's challenge to official
art" (co-author with Julia Andrews) in 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21 – 278
41 《中国极多主义》(Chinese Maximalism )是由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美术馆与中华世纪坛共同主办的。2003年3月14日到3月30日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同年12月5日至2004年2月1日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美术展出。展览图录《中国极多主义》(Chinese Maximalism),重庆出版社,2003年出版。
42 高名潞,《从精英到小人物:大陆前卫艺术的转折阶段》,in Inside Out: New Chinese Art, 加里福尼亚大学出版, 1998,第149-166页。
43 高名潞,《中国极多主义》,重庆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95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