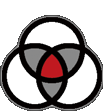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逆向生产——一种前卫介入社会的文化方案 |
时间:2013年4月19日
地点:高名潞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
参与人:王志亮、黄淋、沈桦、许远
王志亮(以下简称王):我想咱们今天通过这个讨论可以理清一些问题,比如,前卫艺术和生产的关系,沈桦作品与后福特式生产结构的关系,黄淋作品与表现主义、贫穷艺术的关系。我2012年上半年在美国访学时曾收到黄淋的个展资料,名字叫“文本·废料·垃圾”。我个人非常关注其中的废料和垃圾概念,拿今天的主题来说就是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谈论的生产相关。我知道在2008年时黄淋和沈桦二位就在讨论参与者的概念,你们能够简单说一下当时的创作情况。
沈桦(以下简称沈):我们在2008年就开始讨论过与其他合作者(非艺术工作者)共同进行艺术生产的问题。2008年我在香港做个展时,每件作品中的一部分就让一些棒棒来书写自己的姓名、身份、来处以及他们在黄桷坪工作了多久等文字。这些合作的因素都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黄淋(以下简称黄):我在2008年已经开始创作《文本.图像.废料.?》系列,通过“黄淋±N位参与者”生产作品,经过作品的实践我提出了“1±N”型艺术生产模式的概念。这里的“1”指艺术家,“N”指参与艺术生产过程的所有的参与者,“±”代表了艺术家和参与者在此种生产过程中的复杂的交互关系。其实,“1±N”型艺术生产模式,是我提出的一种艺术生产的概念,也可以说是我预设并尝试过的艺术生产规则。
王:其实黄淋在2008年的行为作品《KVCIO症》中,也在强调艺术生产中参与者的概念。
黄:最早涉及参与者概念就是那件行为作品。最近,西南政法大学的一本院刊对我做了一个采访,我就提到了这件行为作品,它让我深深地体验了与社会的某种维度的互动关系,激发我后来与参与者一起生产作品,我把这个共同参与的生产主体叫做“1±N生产共同体”。在这些作品中,我把生产过程以及大众的参与环节一并纳入到作品进行思考,在生产过程中寻找突破可能,如何将大众链接到作品生产过程中来,成为我思考艺术的重要环节。后来我的“垃圾装置”(如《人间乐园》、《零度状态》、《“童-言-无-忌-”》等作品)也是这种路径的延伸。
王:我记得黄淋2008年那件行为作品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许远(以下简称许):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机会促成的?
王:当时黄淋请了黄桷坪大街上擦鞋的两位老太太,让她们在展厅中擦拭黄淋的身体。这个过程中,有人就会问,艺术家已经不知道哪儿去了,反而两个参与者成为作品的主体。
黄:那次是我第一次用裸体的方式去完成一件作品。展出后影响很大,很多都是负面的评论,甚至认为是炒作。我当时做这件作品时并没有想过以后的影响。这个作品的方案也是经过了几个月的酝酿和纯化过程才完成。刚开始的行为方案是让擦皮鞋的老大妈用擦鞋的方式擦脚,后来阎闫策划了一个Vital国际行为艺术节,朋友任前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方案,他给阎闫说后,阎闫邀请了我参与。我于是将原来的方案延伸,感觉仅仅擦脚不够,要擦就擦全身,刚开始还想穿内裤(笑),因为害羞嘛!最后还是觉得不彻底,那就直接裸体,更能使作品完成意义的表达。当时公众的反应给我很多启发,其中我妹妹(高中毕业)远在深圳打工,看到网上对我的一片骂声还写了一篇文章“声援”,真切的表达了对我行为作品的理解和支持。这一系列的文化反应让我认识到,传统的绘画作品很难和观众产生这种互动关系和文化反应,当代艺术需要和大众产生更多的互动和关联。我现在也尝试把写作作为我作品的一部分,目前可能更加自信和自如地综合运用各种媒介和资源,包括我和沈桦预设的一个概念空间(正常空间),我们自觉地把一些新的媒介观念转换过来,试图创造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和链接可能。如何去创建我们的切入路径和空间转换,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王:我觉得沈桦在2007年与棒棒老田的一次互相绘画中就已经开始了互动关系的探索。
沈:那是2007年我参加的王林老师策划的“底层人文”展览。当时在宋庄,我和老田彼此现场互相画对方。我们试图在此呈现老田以一个其他行业劳动者(棒棒)如何看待艺术,以及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如何看待作为底层的劳动者——棒棒——之间的关系。老田很久以前就是我的模特,以前从来就只有老田被我画,这次尝试就是探索在互动关系中主客体的不断转化,以及其带来的民主实验。试图打破过去仅仅由艺术家这个权威带来的规则建构(艺术体系),由被动者(棒棒)通过他的画笔建构不同于艺术家的知识(艺术)规则。
王:当时老田身份的多重化引发了很多讨论,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沈:我觉得与当时社会语境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当时艺术市场很好,大家对艺术都很狂热,对各种当时的艺术例外状况很感兴趣——老田当时是模特兼棒棒,在艺术的圈子中很少有这样的人在画画;另一个就是政府也要找典型:以此来宣扬所谓社会主义平等和一种“积极向上”理念。而我们考虑的是艺术可以走向一种工作化的状态。艺术不一定是一群艺术家以某种高地位的姿态来创作,而其他各种行业的所谓一般的人也可以做艺术,就像流水线上的每个人的工作一样,他们在这条工作线上的作用都是平等的。然而,在中国语境中,这个问题后来被引向了其他方向——商业和政治,等过了它的高潮期,逐渐就被淡化了。
王:我们刚才讨论的都是一个“参与”的概念。2008年沈桦做棒棒调查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沈:实际上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基于社会学的概念。我不光是要画这些棒棒,还要将这些棒棒的身份调查清楚。后来这种想法也不断发生了演变:让他们一起来参与作品的制作。这与我当时对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思考有关。早期的福特主义是一种集权式的大工厂生产,每个工人是这个工厂机器上的“螺丝”,而且这个工厂有着极为严密的层级管理结构,这就是专制。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者逐渐从大工厂缩减成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我觉得这这种状况可以用量子理论来解释:即社会都是由独立的个体构成,当要形成一个社会时,关系和规则将这些独立个体链接起来,如果没有链接的话,大家都是独立自主的。这样在做艺术作品的时候,制作的过程可以以此概念来实施。于是就有了棒棒书写的部分。
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与意识形态有关系,例如手机:在专制的国家很难产生手机,有的可能只是高音大喇叭,在话筒前面讲话的是专制的权力掌握者,大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们的权力压制。而民主社会手机的产生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互动,你打给我,我也可以打给你,对话是平等的对应。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价值例如自由、平等会渗透到他们社会的各个方面。相应,艺术概念相对于以前也发生一些转变,包括杜尚用小便池做艺术,我认为这里面也包含着平等的问题,即平常物(小便池)与高雅艺术(画)之间的平等。所以,如何体现一个平等的观念正是我后来做与生产有关的艺术作品的起点。
王:那去年开始你创作的“生产系列”作品也是基于这个想法吗?
沈:是的,当时也考虑到了这些。我觉得今天的艺术不仅仅是一个物平等的问题,还关涉整个艺术生产过程:艺术和社会的关系等,也即艺术家与加工者,艺术与大众的接受等等
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作品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个是你们都强调艺术介入社会;第二,你们介入社会试图建构人与人、人与物或物与物的平等关系。我为什么提逆向生产的概念呢?主要基于这么几点,首先我觉得生产是当代前卫介入社会的一种角度。从广义上来说,所有艺术作品都在和社会发生关系,回应社会的整体状况。我倾向于把艺术家的行为称为文化方案,那么,通过生产的角度介入社会就是当代前卫艺术的一项文化方案。我认为不同的作品可能适合于不同的理论视角,而你们作品所体现的与生产有关的因素,更适合用社会学理论和前卫理论来加以讨论。生产应该属于前卫介入社会诸多方案中的一种。西方前卫的历史其实就是不同介入方案不断更替的历史。达达主义通过选择现成品与社会的关系,苏联构成主义和生产主义通过直接参与社会大生产,把自己作为生产链条中的一部分来接近社会。但是,历史证明,两者的方案都失败了。达达主义的策略很快就失败了,现成品被再次崇高化,而艺术家投入现实生产的举动已演化为当今社会的工业设计和产品设计,丝毫没有独立性可言。后来情景主义国际采取了直接到公共空间创作的策略,新前卫则在美术馆内部展开艺术体制的批判,90年代后的关系美学从接受领域入手,强调作品与观众的互动,为观众搭建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当然,关系美学也涉及生产的角度,例如里克里特·提拉瓦尼亚(Rikrit Tiravanija)邀请观众用餐,这也算是一种从生产角度入手的创作方式。我讨论艺术生产主要涉及艺术与生产相关的诸多因素,如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生产者,又如消费和分配。从这个角度看,你们两位的作品在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方面引入了具有启发性的因素,例如沈桦让其他职业的劳动者来创作作品,黄淋选择垃圾和废料作为艺术材料。
那么为什么是“逆向”生产呢?逆向针对的是一般社会的经济生产模式和艺术生产模式。沈桦的作品虽然吸收了后福特生产的因素,但是却与他有本质的不同。后福特主义相比福特主义流水线生产更加注重生产者的自由,但总体上还是生产者被组织者和最后产品而覆盖。沈桦作品把生产者地位突出出来,同时降低了组织者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讲,他把后福特式的生产方式引入艺术,同时又与后福特主义产生根本差异。黄淋则从垃圾和废料角度颠倒了一般社会生产的过程。垃圾和废料都是我们一般生产和消费的剩余物,而黄淋则把这些剩余物再生产,值得注意的是,我觉得黄淋并没有把垃圾再生产为一件完整的产品,而是保持垃圾的状态,这就避免了再次落入一般社会生产的逻辑。黄淋和沈桦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钟情于手工制作,这里就蕴含了反思当代技术生产的因素。
历史前卫采取的是正向生产模式,他们吸收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技术,采用蒙太奇,用这些技术创造了阿多诺称之为的非同一效果,本雅明称之为的讽喻效果。但是,我觉得今天的问题在于,历史前卫采用新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叙事方式,而今天艺术和新技术的结合还没有给我们带来叙事方式变革的前景,反而正在一步步使艺术走向景观化。
沈:我觉得蒙太奇这种穿插切换的方式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别明显。米兰·昆德拉从几个主角的视角来进行叙事,同样的一个故事,从不同人的视角就有不同的表述,这与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产生了差异。蒙太奇带来的是一种碎片化的叙事,也是民主的机制。它解构了传统的叙事,把线性的叙事分解成独立的碎片,每个碎片不再为组成独一结构而失去自身的独立。
当然,在我们为蒙太奇带来的民主而欢呼时,商业和专制者也在转化蒙太奇,使之为他们的目标服务:蒙太奇也可以撒谎,通过景观的制造对人们的感知进行异化,今天的广告业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模式,我们被包围在它的淫荡呈现里,体验虚假的性高潮。而今天的很多新技术会带来这种虚假的体验,反倒让我们失去了对实在界的感触,而手工的方式让我们能体会到在符号体系之外的物自身的存在——肉体的肌肤之亲。
王:蒙太奇让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式看待世界,电影的发明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正常时间序列之外的东西,例如慢镜头,特写等。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示逆向生产呢?其实也就是逆技术而行,我觉得当代前卫应该和技术保持距离。因为现在的媒体技术并没有突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摄影和电影技术带给我们的认识方式上的变化,反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整个视觉技术就像二维绘画通过焦点透视塑造幻觉一样,为人类带来一个可以以假乱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虚假的。我们可以从现在流行的3D技术、网络媒体技术上看到这些。我们的眼睛完全被媒体所控制,比如昨天书记打车的新闻,一会儿是真的,一会又是假的,它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无法判断,只能依附于网络媒体的传播。
沈: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仿真和拟象的世界。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完全和实物分离了。人的感知被符号所控制,面临的是一个仿真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王:所以,我觉得你和黄淋的作品强调手工,强调人与人、人与物的接触,这就是要求主体在社会中真正接触到物,而不是和物处于一种虚拟关系。现在技术的发展趋势恰恰是要消除我们和物、他人真实接触的感觉。通过艺术作品组织手工生产,我觉得可以让我们重新重视主体和物、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它不是我们所说的经典现成品和装置的概念。现成品和装置只是艺术家去选择和组装,从而消除了艺术生产的制作过程,观众与艺术的关系也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艺术和世界的关系也只能是以观念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以物理的形式存在。
沈:以前的装置,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装置和我们无关,最多我们只能试着去理解它,你没有参与装置所带来的思想建构,没有参与整个过程,也就是装置没有一种互动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前的装置和古典绘画的接受逻辑是一样的。观众只能像瞻仰神一样仰视艺术作品,只能被动地接受。现在的装置更注重互动,而且从生产和接受两方面开启互动的关系。互动是一种接触,而非接受。
王:那么,在互动这方面,我倒觉得黄淋与垃圾“为伍”的过程到是很有意思,你当时为什么钟情于垃圾这种材料?
黄:刚才你和沈桦讨论的艺术作品中的纪念碑性的问题也是我质疑和反思的问题。为什么选择垃圾呢?我觉得垃圾是大家的唾弃物——不需要的东西,让人避而远之,大家因为追求“高雅”都瞧不起“垃圾”,而我把“垃圾”放到一个平等的层面来进行分析和讨论。我把一个被鄙视之物(废料)重新看待,它们是我们“啃食”后的骨头,但它们却成为了我的“需要之物”,进行不断的咀嚼和转换。我把“垃圾”作为一个基本存在物进行了应有的还原和尊重,是对主流消费价值观的一种游离、消解和重塑。“垃圾”在我的生产语境里,它们不是工具,而是一种隔离价值的“平等物”,我在生产过程中,给它们找到栖身之所,发现和实践某种可能存在的关系和结构。
王:垃圾和你以前的绘画有什么关系吗?
黄:我现在的绘画和以前的绘画已经有了根本的差异。以前的绘画感觉很乱,也有些类似于“垃圾”的形态,但却依然是一些感性之物的叠加。而现在的作品,我有一些预设的概念在里面。比如之前我邀请一些参与者,这时我无法控制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情感在我的生产语境里是无意义的,书写出来的东西最终成为“废料”。开始,我是花钱雇佣人参与共同生产废料,后来我的绘画是让我自己去生产废料,我现在的绘画就是从生产废料这个角度切入的。之前可能要一个结果,现在过程成为我作品的必需,我目前的作品仅有生产的起点,但却没有生产的终点,包括装置作品,也不存在终点,如果存在终点,它将消失在不确定的未来。
王:关于绘画和废料,你觉得你的作品最后是废料呢?还是过程中的笔触是废料?你的废料具体是什么?废料的所指在你的装置中很明显,你是在用废料生产废料,而不像贫穷艺术那样,用废料生产高雅的艺术品。所以,我觉得你的装置最突出的特点还是尊重废料自身的物态特征,这就是无序和非同一。
黄:我在生产废料的时候,也在试图和废料进行交流。现在画面中的一条线,我已经不再把线条当作一条线(工具符合)来看待,而是看作一个真实客体(基本物)的存在。在我看来,过程中的笔触和作品最后呈现的形态都是废料的介质,笔触的选择就是对废料的生产和链接过程。线的美学特征这时已经沦为次要,比如我们常说的线条画的帅不帅气啊,流不流畅啊,这些形式化的工具建构逻辑都被瓦解,包括它的色彩本身。我的绘画和装置一旦开始,就没有结束只有“停顿”,因为目前没有一种价值逻辑可以去勾勒废料的终结。
沈:我举得黄淋的作品与今天的社会生产呈现逆向状态。社会生产和社会制度总是把一些资本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抛掉,因为它进不了以价值为基础的流通环节。这也包括难民营里的人,难民不能加入到整个资本生产链条中去,他们已经被商业的社会所遗弃和扔掉。黄淋的作品其实在提醒观众这些垃圾虽然在资本的结构中产生不了作用,但它们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它们有它们的意义。所以,黄淋的垃圾作品可以和一些高雅的艺术作品产生一些对话关系,就像难民营的人走向华尔街与富人走在一起一样,从人的角度来讲,大家都是平等的,同样,垃圾和世界的其他物也是平等的。
黄:这也与福柯的理论有关。我们的整个社会总是有个编码系统,存在着规训系统。我的绘画和装置在重新链接和编排个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正是在强调志亮说的那种无序和非统一关系。世界的权力意志为了统治的需要试图制造有序,包括我们打开网址,哪个放在头条,这些都是有安排的诱导。我在寻求另外一种编码的可能性,可能有些人无法识别我的编码,但是没有关系,我只是提示一种存在的可能和对话关系。
王:差异性就是世界的真实。一个整一和谐的世界可能是可疑的,所以,垃圾的大量存在就是我们世界真实的一面,一般的表征系统却把这些无序与差异都给排除了。
黄:我还要补充一点。你谈的历史前卫的“正向生产”问题。我把高科技的生产看作正向生产,这里夹杂着权力和财富的支配。底层人无法掌握和运用高科技手段,作为弱势群体如何制造和展开一个表达的路径,采用低廉材料和低廉生产方式显得非常重要,比如你说的手工方式,这恰恰是普通人和大众很容易采取和可能借用的一种方式。高科技方向的艺术作品往往只有“成功艺术家”和权贵资本才消费得起的媒介方式。这也是我们今天来讨论和实践“逆向生产”(一种来自民间的和廉价的生产方式)的重要性所在。
沈:高科技也往往带来对人的忽视,机器和计算机往往代替人,形成对人的忽略。这种忽略的表征是技术和符号、图像,把人完全排除在外。今天手工恰恰是说人自身能够做些什么,与实在物有着亲密的接触。
王:这些也与我对80年代以来中国前卫的发展有关。中国前卫的线索来说,前卫系统内部也在不断分化。80年代中国前卫对历史前卫有过很好的模仿,90年代的行为艺术更倾向于一种巫术的效果。巫师代表的是神或天意,观众只能用尊重、崇拜、恐惧的心态看代他们。张洹在90年代的很多作品都带有这样的性质。同时,九十年代还有另外一种前卫模式就是互动式生产,例如王晋的《冰·96中原》就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作品。他把商品封在冰块里,让观众去用各种方式凿冰取物,这时人的欲望表露无疑。
沈: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也在互动上有一些新的效果,她在1974年就创作了一件《节奏0》的行为艺术作品。过程中放了一大堆物品,如枪、剪刀等,可以让观众随意选择物品,随意对待她。这跟王晋作品的互动逻辑一致。
王:确实,他们与我说的巫术式创作逻辑完全不同。
沈:巫术的创作类似于尼采的权力意志。
王:反过来说,我觉得在你和黄淋的作品中,绝对的平等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相对的平等。我们也讨论过沈桦作品和后福特式生产的关系。但是,沈桦作品最明显的特征是完全把作品的参与者呈现出来,让参与者成为生产的主体。这就和现在福特式和后福特式生产模式有了区别,同时也和当前艺术生产由助手和雇佣工人参与的情况区别开来。当代艺术家们纷纷聘请助手参与创作的情况和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坊的运作有着一致性。学徒和助手只能画低技术的部分,关键之处只有大师才能描绘。这里的问题是,艺术家实际把这批劳动力雇佣过来固定在一个岗位进行日常生产和工作。我们现在强调的生产恰恰是给予参与者一种主体性的地位。比如沈桦请工人编制作品,你无法控制最后作品的样式。
沈:这里呈现工人的劳动过程也非常重要。
王:另外,我举得你们两个作品中的参与者并非是一种固定的雇佣劳动关系,参与者做完自己的工作之后,又会回到原来的工作环境中去从事他们自己的生产。这就说明,你们通过艺术,让社会各个分工板块出现位移,促成社会劳动力的流动。这有些类似于关系美学的社会“间隙”观点。我们通过艺术建构一个社会间隙,完成一个不同于社会生产结构的组合。而艺术结束之后,参与者或社会如何运作,那是另外的问题。这也反映出艺术家越来越明白艺术自身的限度,不再寄希望于改变整个社会,这是一个没有结果行为。
黄:这里面我觉得涉及几个问题。一方面,就是“去专业化”的问题。去专业不是非专业化,我们在设置这种生产方式时,降低准入的门槛,这样可以更好的实现艺术的包容性拓展,让艺术融入更多的智慧和能量成为可能。在我的作品生产中,无论什么人,只要他(她)有兴趣参与,在我的作品生产中都有事情可以做。另一方面,就是逐步淡化大众和当代艺术之间的距离和隔阂。
王:你的朋友到你工作室都干些什么?
黄:他们什么都可以干,如来织织网啊,锯木头啊,跟平时的日常劳动很接近,只要你能动手就行,我把作品生产的环节分解成了若干个具体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对于大众来说它是可以分享和参与的。
沈:平常劳动与艺术等劳动之间的平等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人作品中的很重要因素。以前我们总是把艺术劳动预设得很高贵,齐白石一笔就比一个普通的清洁工一扫帚高贵得多。为什么?他们同样是一个动作而已(当然文化附加值是另外一回事)。这里就是我们的规则带来的不平等。但是今天我和黄淋的作品中,比如锯木头的动作与艺术劳动的关系,编东西的劳动与艺术劳动之间的关系,他们实际都是劳动,具有平等性。而且,我觉得自从前卫艺术提示艺术自律之后,它成了社会的子系统,它和其他的东西一起参与建构、影响和组织这个社会。这样高贵艺术就会慢慢地被降低高度,与其它领域形成平等的关系。
王:前卫艺术刚开始时的动机就是拉近和这个社会的距离,直接介入社会生活,所以,杜尚就直接选择社会产品做艺术。这就是比格尔所说的前卫让艺术体制开放,让生活的东西流进艺术。但是,在波普艺术中,它们过分降低了主体性和艺术的形而上学特征。其实,前卫有一部分是去艺术家主体性,和去形而上学化,但是,波普艺术在这方面做得有些过分了,艺术和生活已经无法区分彼此。如此一来,艺术的批判性,文化方案和作用都会消失,最后,前卫和现代主义自律的方案走到了同一个结果。所以,到了情景主义国际和贫困艺术为什么又提出了前卫问题呢?这是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艺术主体性和形而上学不断下滑的趋势,在一个模糊的角度上处理艺术与生活的边界。现在来说,前卫艺术之所能够保持活力,就是在于它既不完全逃入自律的领域,也不会像波普艺术一样无限向生活靠拢。前卫艺术与生活如同两个运动的圆,不断寻找彼此的交接点。
沈:我是这样理解的。当艺术形成一个子系统后,它就成为一个量子,它可以和其他结合,形成一个分子结构,而且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散化,依然是自己。艺术根据自己的立场,与社会交互,为社会提出一些建议。这像朗西埃所说,艺术可以提出一些岐感,提出一些建议和实验性的东西,甚至从另外的角度来组成新的认知(新的感性认知),以此来和社会发生关系。当艺术形成自己的量子后,根据量子的纠缠理论,它实验一定成果以后,会将这种成果模式参与社会的建构,给社会提供一些方案。
王:这就是哈贝马斯对超现实主义失败的判断,他认为历史前卫强行自我开放,但是,此时其他领域却没有向艺术开放,在这种不平等交流的情况下,前卫艺术一定会失败,艺术又会回到自律的领域中。所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对后来前卫艺术有着很大影响,后来的前卫艺术,如关系美学的理论,试图和社会其他领域进行平等对话,让其他领域也向他开放。
沈:早期从包豪斯以来,包括社会主义艺术,艺术进入到大家的生活,比如今天的建筑设计。但是,后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后,他们把艺术建构的东西腐蚀了,对资本生产不利的东西就被抹掉了,有利于资本的东西被拿来不断利用。他们在利用的时候,出发点不是基于人的考虑,而是基于资本考虑。今天前卫艺术应该回过头来重新思考艺术与人的关系问题,思考包豪斯那时所面临的问题。
黄:那天我和志亮也谈到“艺术爱好者俱乐部”的项目,一方面它可以拓展艺术生产的主体,另一方面,它可以去实践另一种艺术生产的组织结构形态,进行长时间的持续性文化生产(逆向生产)。以前的一些艺术项目也可能有大众的参与,但是缺乏持续的生产介入和平行性的结构支撑,而我预设的俱乐部,希望把它做成一个持续性的文化生产和公益介入的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艺术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王: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把一些爱好艺术的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参与艺术创作。
黄:以前的大多数参与艺术都是一次的,而我这个却是一个实际的组织,组织有持续性,人员可能会换,但是大体结构不变,是一个真实运行的结构,也不是静态的几个人,可以和很多事情形成链接,包括媒体,我把这个事情看作超链接。这个组织可能吸引很多人进入到我这个结构。我想与现有的系统形成一个隔离关系,包括用手工隔离技术,隔离消费。隔离不是自我封闭,而是我在保持一定距离时来关照自己、关照我身边的事、物、人和现在的机制。
许:关于垃圾艺术,现在用垃圾作为手段的艺术也很多,像近一点的如王致远,之前我也看过很多艺术家画过垃圾,还有拿垃圾做雕塑。我的问题是你是怎么看待垃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能看出艺术家之间的不同。再一个就是你和他的表达一样,那么你的表现方式的特点是什么?并不是别人表达了,你就不能表达了。黄淋你的垃圾作品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比如我在沪申画廊看到过一位艺术家把垃圾用玻璃罩罩起来,你把它看做雕塑可以,看作什么也可以。黄淋你的垃圾态度是什么?
沈:对于用垃圾做艺术,我觉得有几点:比如贫穷艺术,把垃圾做向了崇高;另一个就是考古式的社会学,对垃圾进行调查;而黄淋的作品提出了垃圾与高雅的艺术物品之间的平等关系。
许:就是说你怎么看垃圾?你想用垃圾来说什么?即便是你和别人一样,那么你的表现方式是否有过人之处,也可以。
王:我在读黄淋作品时比较的起点是贫困艺术。我觉得黄淋选择的材料很有意思,比如碎布,另外,就是这些碎布表现的无序感。黄淋的作品不是去用垃圾塑造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一种抽闲的表达。
许:我刚才在听,黄淋的作品大体有两个诉求,一个是无序感,然后是物的平等。
王: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黄淋对制作过程,如参与人比较在意。
黄:实际我的作品产生了一种关系,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从2008年《人间乐园》开始生产,五年以来一直在自然而然进行生产。我的作品是一种弱符号、弱图像,用一种不明确的意义(或无意义叠加)去消解权力结构和主流消费观。另外,我的作品强调咀嚼,所谓咀嚼就是慢慢地,日常性的,而不是通过某个时刻突然爆发表达一个什么东西。我的东西很零碎,是由若干零碎的个体组成的。它在这样一个共同生产的过程中,逐渐生成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容易流变的临时结构,没有安全感,没有大众所期待的崇高和高雅,只有一种廉价、破碎、漂浮和游离的真实叠化,或者可以说作品最后呈现的是废料生产的某种停顿状态,我的工作就是从废料开始,不断展开废料生产(即一种逆向生产,因为经验的社会化生产中,废料是舍弃物,是一种多余,而我的废料生产逻辑中,原料是废料,生产的指向也是不确定的废料,废料的生产实则是将人们带向了一个抽象的路径和差异价值观的提示)。
王:我当时思考生产这个概念,就认为艺术作品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过程中所调动的各种社会因素。前卫艺术的意义并非在于作品的符号意义,这类思路其实和绘画一样,而是在于作品意义的逃离,也就是能指的无限漂移。比如,我们很难直接从黄淋作品的某一个符号直接解读出一种意义,或从沈桦的编织作品里看到隐喻,确实,意义有时是存在的,但是它却不是重点。他们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艺术作品在生产过程中对艺术体制所改变的一种程度。
沈:其实前卫艺术就是让你不断探索艺术的边界,把原来的疆界往外扩展。我说的扩展可能还是基于艺术自己的领域。它更新着你对世界的认知,会提醒你,可以这样认知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都受到以前的知识影响,比如这是个杯子,以前的知识体系告诉我们这个是用来装水的,但是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杯子摔碎,或是拿来做其他的事情。前卫艺术的作用就是这样。
王:我现在也在考虑如何面对装置的问题。经典的装置是挪用,并用现成品来表达某种意义,比如张洹的作品,他用香灰做佛像。这种类型的装置不考虑创作过程,而是注重最后作品的语言意义。艺术家把物作为工具,去塑造另外的意义,作品依然在寻找某一固定的符号中能指和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这其实和我们去解读一幅图像的意义没有什么区别。反而从黄淋的装置中,我无法解读出固定的意义,也就是说寻求图像稳定意义的方法在黄淋的作品中失效了。例如我了解的一个艺术家马克·迪翁(Mark Dion)创作的《泰特泰晤士河的发掘》就是一个注重过程、研究跨学科的作品,我觉得他最后的展出作品则是次要的。我们可以再回到黄淋的垃圾与其他垃圾作品的对比。同样是用垃圾做材料的作品,艺术家处理的方式不同,作品就有了不同的意义。但是,只要是选择垃圾,就包含了艺术家自己的态度。
沈:齐格蒙特·鲍曼写了很多关于全球化后这个流通的社会,社会如何产生垃圾的过程,包括齐泽克的垃圾美学都说了垃圾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黄:垃圾与奢侈品也形成一种对话关系。
许:那指向无序和平等,是否还有其它表现方式?我觉得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但是用垃圾的更大价值在哪里?
黄:垃圾有个废弃的概念,废弃已经到了极致了。我们一谈到垃圾就会深恶痛绝,垃圾是整个社会边缘化的东西。当人们由于体制和习俗的缘由也有可能被沦为“被废弃的人”,所以,垃圾并不遥远,它有时候就是我们人类自身的缩影。
王:我觉得垃圾很容易让人的感官警惕起来,我第一次看黄淋的这类作品就是感到很不适,这种感觉迫使我思考垃圾的意义。
黄:我想补充一个例子,今天坐地铁,有个残疾人(面部可能被烧伤过)在车厢内乞讨,当他靠近几个中年妇女时,我就注意到她们马上就扭过头去了。正让我看到垃圾(“被废弃的人”)所代表的“肮脏”、“丑陋”都是让人难以相对的。但是我每天都和垃圾在一起,以朋友的关系相处。我有一个体会,垃圾在工作室堆久了以后,也是给人感觉很压抑的,又舍不得扔掉他们,所以,我内心里还在和垃圾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中。我把垃圾提示出来,作为研究对象和生产资料,以交朋友式的方式处理它,那种感觉与谈论垃圾还很不一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