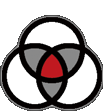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新艺术的启示—— 谈“奇葩”艺术小组 |
—— 谈“奇葩”艺术小组
我们这个时代依然需要深刻的艺术,批判的艺术,建构的艺术!
按:
近日结实三位来自武汉的年青艺术家,他们(杜翌、穆彪、姚钧)自称是奇葩艺术小组的成员。他们的艺术作品显示了当代青年艺术家的一种创作方向,同是也激发了我对未来青年艺术家创作走向的思考。
我总是希望突破以代系划分艺术家的模式,但是却又不自觉地关注这一批新兴的青年艺术家。如何突破这种代系划分模式,我想有一点可供讨论:新的艺术倾向不一定必然出自青年艺术家手中,老一辈艺术家也可能创作一种新的艺术。我们如何评价“新”与“旧”,主要要是以艺术家的创作方法论为依据,而非艺术家的年龄。但是,如果这样划分,我们又会不自觉地落入“新之崇拜”的陷阱,因为艺术有时不能以新旧作为衡量标准。艺术总有的它不变的精神内核,比如深刻性,批判性,艺术家的人文意识等,所以,当我看到“奇葩”艺术小组的作品时首先想到,艺术这些美好的品质依然存在于他们作品中,然后才去分析其作品的特征和当代意义。
现在很少能够听到以小组为形式活动的艺术家,“奇葩”算是少数当代艺术小组之一吧。80年代是小组、画会、社团活跃的年代,85美术运动的中,如谷文达、吴山专这样单打独斗的艺术家实为少数。80年代艺术家之所以以小组的形式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交流欲望,小组是一种能够保证他们进行交流的组织形式,另外,80年代需要解决的不是个人主义的问题,而是哲学意义上“人”的问题和一些依赖于思辨才能得以继续的哲理性问题,所以,小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但是,90年代,随着艺术与哲学之间的纽带被撕裂,国家意识形态的紧缩,艺术家对思辨能力的抵制,小组形式随之破灭,而出现了以艺术家聚居区为主的画家村艺术。中国当代艺术的后二十年,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个体艺术家,而非流派、小组和和社团等集群形式出现的艺术。
仅就组织形式上来看,奇葩艺术小组采用了一个过去式的形式来进行艺术创作,但在当前来看,却是恰当的一种组织形式。奇葩所进行的一系列艺术活动都必须依靠集体的合作、智慧才能完成,从方案的提出到现场实施,再到后期制作,这是一种团队合作模式。他们与80年代小组运作方式不同,80年代小组基本只作为一个供艺术家彼此讨论艺术和组织展览的团体而存在,但奇葩的功能不仅是供艺术家彼此讨论作品方案,而且他们之间各有分工,比如影像拍摄,模具制作,后期影像剪辑,效果图制作等。这种方式不能不说是当代社会发展所带了的艺术小组功能的扩展。
奇葩艺术小组的艺术作品并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艺术样式,而是涵盖了绘画、装置、行为、影像等一系列当代艺术表达方式。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挑战早已超越了现代艺术和后现代交接时期的材料问题的局限,各种艺术表达方式已经处于同一起点。艺术家创作所采用的艺术形式已经不能用来作为前卫和非前卫的创作标准,已被定位为传统的架上绘画同样可以成为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无论艺术家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创作,只要再现了他的观念,这个观念又是当代性的,有效的,那么其作品就可以说是成功的当代艺术作品。奇葩的作品正是基于这一观念,才没有受到材料的限制,物尽其用,一切都可能成为他们的艺术语言。
奇葩艺术小组成员是三个穿梭于城市空间中的“异行者”,他们的艺术专为都市而生。都市的选材角度让他们的作品即熟悉又陌生,因为在80年代后半期和九十年代,都出现过针对都市而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但是,相比而言,奇葩的作品却是我们这个时代都市的产物,有着绝对的时代特色。中国的80年代并不存在真正的都市,所以,85美术运动中的艺术作品没有多少去体现都市情怀,而是回归人本身,回归哲学,仅有的“池社”、“观念21”和“上海布雕”等艺术小组的活动,只能算是发生在“都市”空间里的艺术,他们在意的多是艺术语言本身和人问题,比如池社的作品“陈式太极”首先是要让艺术回到大众,与大众有直接沟通,其次是艺术家要享受创作过程中的“浸入”感;“上海布雕”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突破雕塑的材质限制,并将雕塑置入不同的空间,与观众直接交流;“观念21”则更多地注重宗教和哲学的表现。80年代这些小组对语言的尊重其实是符合了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转换时期语言更迭的规律。90年代的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都市的概念,当都市刚刚兴起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拆与建”,所以,此时的许多都市艺术都是以都市拆建为题。
奇葩的都市艺术不再遵循八、九十年代艺术家与都市相和谐的创作方法,而是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作品强行嵌入社会结构,并对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冲击,所以他们的艺术很多情况下都在权力的干预下被迫停止。比如作品《马赛克》,艺术家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将街区中的变电箱涂成马赛克图案,以表示自己对这种影响城市美观的物体的反对态度,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这是让个人愿望参与到实际的环境建设中的主动宣言,这种要求与人民要求民主权利一样急切,我们对美的要求是属于乌托邦似的。”《释放我的世界》是一件更具挑战性的作品,他们直接将城市公交站的广告牌换成自己制作的反商业海报,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回应广告对公众视觉的野蛮入侵。
强行嵌入的创作方式体现的不是艺术家对意识形态的反感,而是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来自于艺术家对艺术的纯真信仰。年轻艺术家的这种“公民意识”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段自我建构和青年人的心智逐渐健全的表现。他们的这种表现要远远超出九十年代所谓的主流前卫艺术对意识形态的调侃。九十年代的主流前卫艺术是艺术家思想溃疡的表现,包括栗宪庭到处拿意识形态和反意识形态说事,这其实就是农民式的思考问题的方法论。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对抗意识形态,而是首先明白自己作为公民的身份,寻找途径去建构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而不是一味地作为意识形态的局外人冷眼旁观,因为旁观者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笔者前段时间已经提出了川美青年艺术家的三个倾向,现在看来,这三个倾向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域的青年艺术家,奇葩就是属于“社会批判类”。此处的社会批判已经不再是画一个老农民以显示农村人的疾苦等如此简单的创作逻辑,而是身体力行,与社会发生直接冲突,将自己的艺术主张强行推给社会。他们也不同于那些简单的拍摄乡村、工人苦难的摄影艺术家,而是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自己进行实施。所以,我认为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超越了反映论的创作模式,去“反应”而非“反映”都市现实。反映论的创作模式是中国当代艺术多少年来挥之不去的顽疾,85美术运动的产生,最重要的成因就是对反映论的厌恶,不幸的是,90年代当代艺术在某些持庸俗反映论的理论家手中又回归了反映论的创作模式。前一两年兴起的卡通和图式绘画批评浪潮正是对反映论复辟的再清理。奇葩为我们提供了摆脱反映论的一种艺术方式。他们有着鲜明的艺术主张,作品的实施不再是单纯地反映社会,而是为实现自己的主张不得不进行的创作。
奇葩的出现是整个庸俗商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的每一件作品都与都市有关,更进一步是指与都市中的商业有关,但是我们在他们作品中却看不到肤浅的商业符号。奇葩的艺术无疑是深刻的,这种深刻性的表征是社会学的批判,哲学式的深刻已经隐藏在了其社会学表征之下,贯彻他们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奇葩的出现必将让那些认为青年人只会表现无聊自我的观点不战而退。
王志亮 2008年11月19日 南十里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