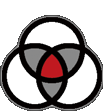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风情与超风情 |
观《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全区美术作品展》随笔
一提到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人们就必然想到“风情”。维族是充满装饰的“风情”,藏族是原始素朴的“风情”,蒙族则是牧歌式的“风情”,……于是,“风情”成为少数民族生活的概括。千里迢迢“深入生活”的画家,其志多在于“采风”。土生土长的画家,也将“风情”作为本民族和本区域的特征,以别异域他族。甚至并非少数民族,像巴山、陕北、湘西……凡边塞僻壤,各有各的“风情”。扩而广之,江南北国也自有“风情”。“风情”,如果抛开它的原始意味,按目前一般的理解,就是风土人情,包括风俗习惯、地理风光、人的风采情趣、男女风月之情等等。它是一个区域、民族的文化的表层特征,它具有一下子抓住异域他邦的好奇心的魅力。
诚然,“风情”是客观存在,但它不是一个民族、区域的全部文化、生活的概括。在“风情”以外,“风情”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精神因素。但是,“风情”的魅力诱使一些“艺术家”满足于视觉经验的描述,反映生活停留在新奇的场面和稍加变化的“形式”上,造成了一种“风情”泛滥的局面,使人颇有厌腻之感。
我们不排斥表现“风情”,而是说,“风情”不是一切,而且,“风情”本身亦有层次之分。
即如内蒙草原,似乎充满诗情画意,蓝天、白云、嘹亮的牧歌和激扬的马头琴,富于浪漫色彩的套马摔跤:剪羊毛,……成为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表现题材。然而,蒙古族并不是仅仅像欢快的牛犊那样生活,她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有着深层的和复杂的多方面。当初成吉思汗对百官之训言可以窥见其性格:
闲暇的时间,要像牛犊。
嬉戏的时候要像婴儿、马驹!。
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
高兴的时候要像3岁牛犊一般欢快!
同敌人对阵的时候要像黄雀一样节节跃进,
饥饿的老虎一样,愤怒的鹫鸟一样!
在明亮的白昼要像雄狼一样深沉细心!
在黑暗的夜里,要像乌鸦一样,有坚强的忍耐力。
(引自[日]小林高四郎著《成吉思汗》)
是呀,我们只要了解一下蒙古族的既有屈辱和失败,又有征服与荣耀的坎坷历史,就不难理解马头琴那深沉、悠远的长调的意味。它既有悲怆伤感,又有坚毅、兴奋和欢快。它是愁与乐、回忆与憧憬的和弦,而马头琴也正是少年苏和为解除寂寞和仇恨,寄托对自然造物的纯真之爱的回忆而作的。(见《蒙古民间故事选·马头琴》)
我曾有幸在内蒙乌兰察布草原与牧民共同放牧生活5年。如果有人问我,草原的最大特征是什么?我就回答:“孤寂。”不是么,山坡、云、蒙古包,甚至畜群,在广漠的空间中,静静地躺、悬或嵌在那里。人的一生时光大部分是在一个人的情况下度过的。那达慕和剪马鬃、剪羊毛一年只一两次,那是牧民的节日,而一切欢乐、伤感、幸福都在孤寂中孕育,在孤寂中等待,在孤寂中品尝和回忆。孤寂与蒙古族坚毅的忍耐力连在一起,孤寂将牧人与天、地、一切自然造物合为一体,从而使它既像“苍狼”一样深沉,又像白鹿一样单纯。就是这蒙古族世代吟诵的祈祷——蒙古源流的传说:
“——天上有命,一位苍狼,他的妻子是雪白的鹿。他们从一望无垠的大湖对面游过来。斡难河水流经不儿罕山,诞生了英勇的巴塔赤罕。”(《蒙古秘史》开篇,采用[日]井上靖《苍狼》译句,中译本张利,晓明译)
蒙古族是爱好抒情的民族,然而其情却不是文人的吟风赏月,而是朴素的史诗、英雄的赞歌,《蒙古秘史》就是值得骄傲的民族英雄史诗,它语言单纯得像处女,内中充满格言、诗句、谚语,在平易中显出力量和雄浑,它像北魏时流传在今日土默特平原的游牧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妇孺皆知的诗歌,而今谁解其中味?到底是悲怆、伤感、自信、漠然,还是孤独?不可知,但可以肯定它绝不是什么诗情画意,内中有着朴素、深沉的自然意识。史载北齐高欢为周军所败,曾使敕勒族人斛律金唱此歌以激励士气呢。后来,唐朝一个边塞诗人吟出了一首与之相匹配的绝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者在对天地的爱与畏的赞颂之中投入自然,人没有感到孤独。后者则意识到了自然与人的某种对立,虽然与前者一样吟诵了宇宙的博大,而人却感到渺小了。
不论白天、夜晚,只有苍天。天地以外,泯然无物。宋人赵珙《蒙鞑备录》谓蒙古人“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敬天之例在《蒙古秘史》中屡见不鲜。他们既不像藏族受佛教原则所维系,也不似汉族为伦理秩序而束缚,而有着更泛神的自然原则。蒙族起源除上述苍狼白鹿之说外,还有“感光”一说,即成吉思汗孛儿只斤氏族的祖先孛端察尔是“感光而生”的天子(见萨襄彻辰著《蒙古源流》)。虽然16世纪开始传入蒙族中间的喇嘛教(黄教)总想以佛的至上观念排斥蒙族本土萨满(蒙语布克)崇天的自然神观,但蒙族的传统敬天思想仍然很
浓,蒙语“腾格里”既谓天,又指神。
这种自然观导致蒙族对自然物的爱和畏,他们祭天、祭敖包,爱马、爱牛,……
画马,于是就成为蒙族的永恒题材,很早,在13世纪以前,蒙族就把“天马”旗悬挂在蒙古包或敖包上。上用文字写着天马从太虚幻境带来的幸福。因此,马不仅仅是可以跑的马,它还有精神性,画马也不能徒有其表。其实岂止蒙族,汉族早在唐代就有这样一种立论了:杜甫批评韩干“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在这次《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美术展览》中,青年蒙族画家海日汗和丹森画的马就多多少少赋予了某种精神性于其中。丹森《走马》图中牧民斜侧的身躯与略夸张的走
马恰到好处地画出了步履如飞而又平如船行的感觉,但单调的不断绵延的草坡却使怡然之趣也变得单纯,一切情感心理被排斥掉了。走马是马中之马。人与马在互相制约中融为一体,而头脑中是空白,空白面对着漠然的天地,这时只有存在与非存在。这张画使我又想起了浙江美院85届毕业生张克端(来自内蒙)的雕塑《冬季的草原》。海日汗的《马》(国画)却倾注了作者的爱,他极力想把马画得单纯些,尽力去掉马的动物属性,加进自然的灵性。蒙族虽没有“乾为天,天为马,地为坤,坤为牛”(《周易》)的直喻,但神马的传说世代流传。
鄂温克青年画家维佳画的《采蘑菇》有一种特殊的神秘味道,枯木槎桠的超现实场景却是一种现实生活的背景,一个采蘑菇的鄂温克妇女神情专注、怡然自得于自己的劳作,“冷峻的现实”对她们无动于衷,自然的枯竭与人的生命欲望之间的冲突何等强烈,然而作者把二者处理得那么和谐,说到底,在纯洁天真的眼中,一切现实都是“和谐的”。作者表现的是额尔古纳左旗敖鲁古雅地方生活的亚库特人(鄂温克族的一支)的心理和情感。他们对这些枯树、死树的“视而不见”的情态,对我们而言是很难理解的。据说这一支现在还有一二百人,他们是森林地带的“狩猎民”。蒙族自古也分为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二者在生活方式与文化方面均有差异。他们又与都市文化有更大差异,这差异造成的神秘和不理解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从内蒙到中央美院读研究生的苏新平近期画了一套石版画,也有超风情的追求,当然仍带有风情的印痕,他是从风情中走出来的。他的人物造型简洁拙朴,健康、充满活力。运用
光影很熟练,概括力强,因此光影使物象与“感觉”分离了,静寂的世界是明确的。这种理性因素强化了民族的“孤寂”特征中的丰富性。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在草原,牧民迎接客人的除了奶茶点心,还有沉默,彼此相顾无言,靠静寂中的默契神会交流,“也许唯有能与他人真正结合的人,才有这种孤独于宇宙之间的外表罢”([英]戴·赫·劳伦斯)。这“他人”对于蒙古人来说即是自然、是朋友,这时,他们是忠诚的,说谎与偷窃于他们无缘,甚至喝酒亦得酩酊大醉,不耍奸方够朋友。但对敌人他们也会诡诈,在沉默中、等待中伺机以惩。而这些,早在13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出使蒙古游记《蒙古史》第四章就有“关于他们的性格(好的和坏的)”的详细记述了。
因此,风情不但涵盖不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更不能揭示其深层文化和心理。浮光掠影的“采风”,搜奇猎异,会助长部落文化的保守性,其心理是只满足于充当供它民族猎奇的博物馆。这不仅仅对少数民族而言,整个中华民族亦然,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有形式的、直观的文化和精神的、信仰的文化两个方面,这两种文化,又可以称为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风光、习俗、奇异的祭礼等等是有形文化,即通常我们所指的风情,无形的文化则是指语言、性格、心理、宗教、信仰等等文脉结构。前面我们谈到的蒙族的非风情的方面均属无形的文化。
无形文化应是艺术表现的更重要的领域。以感悟的形式,显示民族的观念、民族的心理和意识及民族健康向上的力度。一旦悟出那微妙的深沉之点,自然会与某种有形文化的特征连在一起,而后技巧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有形文化对造型艺术有直接的诱惑力,特别是对形式偏爱的艺术家,常会激动不已,这激情会使他认定有形文化即是内容,从而标举为该民族该区域的普遍特征。同时,某一成功
画家的“风情”样式会导致一种普遍风尚,而从大范围看,我们的“最原始的即是最现代的”(现代加民间)的“风情”还不是从毕加索、马蒂斯那里来的么?
这次内蒙40周年大庆美展,如果与1983年在首都举办的以“风情”为特征的“草原风貌画展”相比,已见明显不同。
这次画展,“风情”作品虽然仍占多数,内中也有一些乏力之作。但更重要的是,已经出现了超风情的趋势和在风情表现上多种形式风格的探求,特别是油画,面目还是比较丰富的。
既然“风情”是直接介入人的视觉和情感体验的表层特点,那么它就应该包括:自然形式的、纪实性的、趣味的和抒情的等等多种角度。
当然,我们强调艺术深掘无形文化,并非是指艺术等同于民族学研究,民族艺术毕竟是有别于民族学的一门学问。除了外部形态和思维形态的区别外,更重要的是,民族学的研究
主要着意于过去,即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民族。当然,从本质上讲,一切历史也应是当代史。而艺术毫无疑义是属于现代人的,复古亦为开今,它是现代人的心理观念和情感的写照。于
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即摆在面前,如何对待民族特征与现代文化、区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的关系?
20世纪民族学中的德奥历史学派(或称德国文化圈学派)的创始人格雷布内尔提出了“文化圈”和“文化层”的概念,即具有相似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民族同属于一个“文化圈”
(空间概念),而“圈”“圈”重叠便成为“文化层”(时间概念)。此派学说反对进化学派的人类具有共同文化发展规律说,认为整个人类文化史只是几个少数优秀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几个文化圈在地球上移动的历史。此说虽有机械结合和文化沙文主义之嫌,但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文化在传播中竞争、生存、发展的真谛,因此,它又称为文化传播学派。
曾有人以乌龙茶比咖啡好,说明民族的即是世界的道理,但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这只是一厢情愿。咖啡不但作为饮料,同时也作为文化传播媒介进入中国的。或许不少自诩具有现代文化的人虽喜茶,但他必须得品尝和认识咖啡,这种强迫你接受的力量显然乌龙茶不具备,要想使乌龙茶战胜咖啡,不仅要保持乌龙茶的质量和纯度,更重要的还得使乌龙茶的背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强大得使人以接受为荣耀才行。
因此,一个严峻的现实即是,只封闭地保持民族特点,是不能自强的。不能只把自己的文化局限在民俗的层次上,即基层文化的层次上,还应创造具有扩张力和包容性的上层文
化。一方面挖掘强化固有的精髓,同时要赋予其现代精神,使它能与现代诸元文化对话、抗衡。为什么我们就只能以表面的“风情”取悦于人,而不能也表现我们的抽象思维、生命冲动和对世界的解释呢?难道因为“没特点”我们就不能骑摩托、穿西装、住房子,就不能搞现代艺术吗?多少万年前大家都在群居和打磨石器,而今天任何诱人的文化都是人类智慧者的创造,羞于拿来不如放胆引入并做出更好的来。也不必妄自菲薄,似乎少数民族地区就不能搞现代艺术。
所以,必须立足两极,一方面,深掘民族意识的精髓,另方面,唤醒和强化民族的走向未来的意识和生命力。没有前者,后者无根基;而无后者,前者也会萎靡。二者是互补的。所以我们应创造出深沉的真挚的民族艺术及同步的高层次的现代艺术。而现代民族艺术的根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的寻根,它应是敢于展示自己维护民族与超越民族的内在矛盾的勇气,唯有经过这一胎动,新艺术才会降生。艺术不只是美的点缀,更多的是人类的生命力的补剂。美与多情的民族使人爱惜、怜悯,深沉亢进的民族使人敬畏、爱戴。同是爱,力量与程度
殊异。
我希望蒙族和全中华民族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