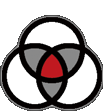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消解的意义——析当代中国文字艺术 |
在近年的当代艺术作品中,汉字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表现题材。谷文达、吴山专、徐冰、邱振中都创作出了很有影响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在试图改造、修正、消解传统汉字,创造新语义和新形式的意图与手段方面有着内在一致之处。本文不探讨作者的表现意图,也不对作品的文化涵义和审美趣味做出判断,只对作品的构成方式和手法进行分析和描述。
选择汉字做为形象媒介的意义
几位艺术家选择汉字做为题材无疑是因为汉字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符号在形象结构和语义方面有着无尽的可塑性。首先是其具有形象性的抽象结构。唯独中国保留并发展了文字艺术——书法。然而,汉字之所以保留下来,书法也能发展起来,却并非因其形象性(在六书中称为“象形”) ,而恰恰与其表意功能相关。汉字是表意文字体系的代表。汉字的单字造形从本质上为表意而非表音,因为它不是一个拼音字母,它本身就是一个音,但音与字本身的意义无关。意义主要与结构(即形象)有关。六书中“指事”、“象形”、“会意”即是汉字表意特征的概括。正是因为中国的象形文字表意和音响在结构上是分离的,所以,中国的象形文字才得以保留下来,而埃及的楔形文字的象形符号中有很多不是表意而是表音(符号的作用是一个拼音字母亦即相当于音标),于是它在西元前500年时就迅速地变为拼音文字了。
由于汉字的符号为书法提供了完美而又无须再创造的基本结构原型,所以书法的创造只在单字结构上进行微妙的变化改造。其天地主要在笔法和章法,其笔法强于章法,因为笔法与结体组合微妙地显示出艺术家的情感和心理的轨迹,这是书法的主要功能,而书法的次要功能才是二维平面的整体结构和理性布局。所以,章法弱于笔法。同理,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墨法弱于笔法,因为墨法偏于理性构成,笔法偏于情感表现。
汉宁结构的稳定性决定了书法艺术在结构创造上的惰性承传,然而,汉字结构原型的保留又并没有逐渐强化书法中的语义的丰富性,相反,书法的题材越来越经典化,诗、词、歌、赋、铭、序、经中的许多经典世代相因,成为书家必书的题材,如《归去来辞》、《千字文》等,故人们从传统书法中获得情韵的途径主要是笔画和间架,而非语义本身(当然不是毫无关系)。一个书家的风格一旦固定,仟何题材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于是,传统书法为现代书法家设置了两个难于逾越的山峰,汉字的单字结构的稳定性和语义的经典化、程序化、模式化。这两点如没有大的突破就不可能激活现代人的眼睛和心扉。于是,消解汉字的单字结构和经典而又附庸化的语义即是从事现代文字艺术的人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旦进入消解,就会发现,消解单字结构必定带来消解传统语义,而消解传统语义模式也必终导致消解单字结构。
消解手段的比较
我们会发现,谷、吴、徐、邱几位文宁艺术家的表现手段就离不开上述两方面的消解手段.
谷文达的“字”,开始想从破坏单体字的结构入手,同时仍保留书法的笔法,如“神易”。后来发展为错别字、倒字。但这种破坏其实是表面的,因为不论你怎样按部首拆开单字,都仍保留着汉字的“字源”,即偏旁,而偏旁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字,甚至早在唐代开始即有人研究形旁,当时把会意、形声等复体字中的形旁视为汉字的“字源”,并把这方面的研究叫做“字源学”。当然,谷达的“字”非为文字学研究,其目的仍在造形,破坏了习惯性结构(形体解放)带来了造形的自由度,错、别、反字的结构趋于纯抽象性审美结构,但不彻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迷阵”,反常规的文字连缀阻断了部分常规语义的通道,不可解的空白产生了新语义,但谷文达的消解始终徘徊在形与义之间,两方面均未走向极端。即使是他后来的观念化较强的无标点、或错断句的字亦如是。
吴山专等人的《红70%、黑25%、白5%》(以下简称《红、黑、白》)和《红色幽默》中的文字显然与谷文达有类似之处(不论谁影响谁)。但吴山专的汉宁一上来就排除了书法的抒情因素,全用黑体字写就,他造了许多高明的简体字,也造了一些认不得的字,他崇拜汉字的结构美。但他并不只是专注于单字结构之美。其文字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创造“新语义”方面,因为他一般不破坏单字结构,而且还随手拈来日常语言或书面语言的字、词句,“偶然性”地将它们搁置在一起。不相关的搁置导致了语义的陌生感,陌生使通常语义引发的思维模式的流程中断,遂出现“空白”。这时联想开始填充“空白”,“空白”越大,联想越丰富。比如,他将“涅槃”与“垃圾”并置在一起,又创造出像“庄子的蝴蝶是一把剪刀,什么地方要什么地方卖”,这样的很荒诞的语句。还有“秃鹰飞离了天丧台,台上到处是柯达胶卷”等。以“垃圾”、“涅槃”并置为例:
常规语义
垃圾:肮脏、低劣废弃物品、蚊蝇遍地、污秽之地
涅槃:圣洁、不生不灭、圣乐仙花、不生不灭
“垃圾”与“涅盘”并置违反了常规语义,但并不等于不产生语义。
禅意 反叛 信仰危机
↖ ↑ ↗
垃圾←——————————————————————→涅槃
↙ ↓ ↘
荒唐 亵渎 嬉皮
这种新产生的语义联想是由特定话语社团的语言模式所规定的。或许在不同时代的有些地方,由垃圾可以想到崇高,但在我们话语社团中这是不可能的。而“垃圾”、“涅槃”也使这些概念在话语社团中不是孤立的具有封闭性内容的概念,它与许多和其相关的联想概念织成了一个结构网。德·索绪尔曾举例说明这种现象,当我们听到或看到“一个男孩踢了一下女孩”的句子时,我们会想到“不是吻或杀了女孩”,这里“吻”和“杀”就与“踢”形成为语义关联的结构网。换句话说,没有“杀”、“吻”这样的动词,也就无法确定“踢”的动词涵义。正是索绪尔的这一发现,否定了传统语言学将每一个词视为具有固定内容,而词与词相加只是不同内容相加的观念。这导致了哲学、语言学、艺术等领域的一系列革命。
正是因为这种话语社团的特定语境所规定着的结构网性质使吴山专的非常规语义并置产生了各种“空白”,而“空白”又产生了各种更丰富的意味,反过来这联想意味又丰富了结构网。
当然吴山专并不只是在这里作诗,玩文字游戏,他赋予文字以辅助形象,比如将“垃圾”与“涅槃”组织成一个三角形。字在这里的编排不是按照书写(信、诗、散文等)格式,亦非“书法”格式。而是按绘画性规则配置,更重要的是,黑、白、红的大色彩对比向观者提供了更醒目的“直观空间”,它直接刺激视觉,产生共时性的第一感受。而文字配置得到的语义联想是“时间流程”,是历时性的过程。当它们融为一体时,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心理即形成了在反差中的统一,如是“红色幽默”形成。尽管此后吴山专创作的“红色幽默”的大字报和广告的铺天盖地,较之(黑、白、红)更为普遍,但其基本手段是类似的。
做为装置形式的作品,徐冰的大模样与吴山专相类。但徐冰《析世鉴》的基调取传统文人黑白雅素的书卷气,吴山专则取“通俗”和“革命”的“痞子”风格。在消解手段方面,徐冰对字义的消解既不靠谷文达的拆字、倒字等变化,也不用吴山专保留字的原型,阻断字义连缀通道的方法。同时,他的字既不是谷文达书法的字,也不是吴山专通俗流行的黑体字,而用宋代木板刻字的字,字的排列也是规整、平均、清晰的,完全是一本正经的书卷样子。由于字的大小、面积、笔体都一样,遂取消了观者可能由于字的位置和比重等形态因素的差别引发的主次感,而这种主次感会导致观者心理发展的时间过程。正是这种一本正经和平淡无奇的假象,首先抑制了人们的好奇心,而被其整体视觉空间所滞留。然而,当人们合逻辑地去读其文字时,却又一个大字也不识。知识积累和文化经验的断裂又一次令观者失去好奇心的焦点.从而产生茫然、不可解等心理空白。人们再不能像看吴山专的字时那样去联想和填充具体的语义,也不能为其择句的机敏和灵动而会心一笑或点头称道,更不能像看谷文达的字时那样去猜字或重新断句。因为,徐冰的字是根本认不得的非字,但不一定不是字,它使我想到西夏文,乍看是汉字,近视认不得。当然,徐冰的字很有可能于某天与考古发现的字在结构上谋合。
这众多的非字合成一个无意义的巨大空白,但这不等于徐冰心中是空白。因为他时刻得想着不能刻成某个字,故胸中不离非字之字,亦即不离实有之字,空还是出于实。当然,谷、吴的字之变,语词的不合理配置也是出于模式之实,但关键在于实与空的反差强度, 既保留汉字的基本特征要素,而义又将它的结构和语义抽空实在不是易做之事。显然,从消解字的结构和字义的效果看,徐冰是最彻底的,由于单字消解彻底,必然导致字的纯结构形成。彻底排除了表意后,得到了纯造形。非字的纯造形合成的巨大空白为人们提供了美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文字学的各种阐释角度和意义,但在徐冰,则可能是始料未及的。
徐冰消解模式: 文 虚 过
化 无 程
与 与 与
…… 宿 传 果
……非字…… 命 统 结
……非字+非字……. ↑ ↑ ↑
……非字+非字+非字……——→ 无 意 义
……非字+非字…… ↓ ↓ ↓
…… 非字…… 字 庙 书
…… 海 堂 象
(非字≠不是字) (无意义≠非意义)
吴山专与徐冰“空白”生成模式比较:
空白
吴山专字、词、句←→字、词、句
徐冰 非字相加 ←→ 空白
吴山专依靠等量并置的字、词、句阻断常规语义获得“空白”。徐冰则以平均等量相加的字在量上的“无限性”获得“空白”的无限性。
邱振中的消解过程
与谷、吴、徐不同,邱振中是以书法家的身分写字的.这无疑名正而言顺。邱振中的(最初的四个系列)也确实在突破传统之时,又力图固守传统书法的最后边界——笔法和章法。所以,邱振中之字较之谷、吴、徐之字更像书法。但是,邱振中对单字结构和字词语义的消解却与传统大相径庭,而与谷、吴、徐有着一致性,而且邱振中的消解过程也恰恰囊括了谷、吴、徐二人消解的不同手段。
我猜想四个系列的产生顺序如下:新诗系列——语词系列——众生系列——待考文字系列。
强化现代平面构成意识
传统书法是心理主义的创造活动。笔法和章法是情感心理逻辑的物化形态,书写的题材也是为此服务的。书写时任情所至,虽也加以控制,但二维平面的严格设计和谨严布局意识不强,偶然性强。邱振中的“新诗”系列想以横写格式突破旧体诗词书法的“抄录”感和简牍、信札的例行公事的样子,并保留墨迹渐淡的自然效果,字迹随意性强,极力摆脱传统行事草书规范,以横向行轴线为排列的基本定向和位置,尝试形式构成的纯粹性(见〈新诗系列.代B答〉) ,但由于作者仍保留着传统的心理逻辑发展的特点和意境体验的表现方法,故此系列的突破性并不强烈。
消解意境
意境不等于作者主观要表现的东西,即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讲,意境恰恰是主观意图非明确表现的“空白”所导致的涵义。我们时下的书面创作常常以个人的心理经验为“意境”,并强迫自己进入所谓的“意境”之中,于是浅薄和造作比比皆是。通常理解的书法“意境”的原材料当然来源于字、词、句、诗、文的语义以及与此语义相适的造形意趣。邱振中以消解常规语义的手段打破了传统书法“意境”的语义模式,择取“汉语词典以三角为词头的词”写成了“语词”系列中的一幅作品。(见〈语词系列·汉语词典以三角为词头的词〉) 。词典条目似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集合,你一言我一语没有必然的语义联系,然而并非绝无联系, “三角”是中介。这种阻断常规语义(如三角裤和三角洲没有必然的联系)造成“空白”的消解手段与吴山专类似。邱振中又赋予这种文字以即书即画的造形效果,但毕竟笔情墨趣已不为传统的“意境”服务,从而更为独立一些。对于作品的涵义,邱振中认为是:对当代语言学和当代哲学的思考,对弗罗伊德泛性欲主义的反思,对生活中秩序与荒诞的感触等。这里不作分析,观者自可由此去想象和验证。
消解语义规则
如果说,邱振中在“语词”系列阶段只是感到不搭界的语词并置在一起所产生的空白中有一种神秘的意味,而这种效果又是偶然性的题材导致的。那么,到了“众生”系列阶段,他已自觉地意识到:“当人们交给你二十个意义不联贯的汉字时,你根木不知道应该怎样排列。事情的另一面是,规则已不复存在,你可以将它任意处置。”于是,“百家姓”、祖母念经时重复无数次的“南无阿弥陀佛” 、每天签名的“日记”就成为众生系列的题材。把规则束缚拆掉,获得了单字排列的自由,取得了纯形式结构的效果,最明显的是〈众生系列之1〉,将“百家姓”的各种姓字在方向、位置上随意颠倒排列,并分布为浅淡和浓黑的两块,其平面构成方式巳近于版画,〈日记〉亦然。不过,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本来“消解”乃是对书法本体问题的质疑和诘难,所以“消解”的造形形态也应体现出这种难题意味,“消解”的目的绝非为了走向纯抽象形式的绘画,尽管“走向结构”的方向是对的,但如果字的结构完全等同于绘画中的线条作用,那么则又反过来消解了“消解”本身的哲学意味。所以,字在这里也就不过是一种参照题材或形式的材料而已。这是邱振中“众生系列”仍嫌单薄的原因所在。
消解的结果必然走向“待考文字”系列
在此之前最大程度的消解是随意抽取单字,避开语义,但这些单字倘写得清晰可辨,就会产生新语义,倘不好辨认,又等同于纯线条,这种限制对于欣赏者或许无所谓,而作者则总会被单字的语义和结构模式所干扰,产生心理障碍,从而不能较纯粹地进入结构性的创造。 (这里的结构并非指纯形式,乃指作者的意图、作品、作品进入交流领域中产生的涵义诸因素的有机关系)。于是,邱振中选取了先秦货币待考释文字为母题,取待考文字本身是字又非字的文化意味,但在复现它们时又不受这意味的干扰,可以进入纯然的组织和书写工作中去。在“即字非字”的特点方面,邱与徐冰的字相类,但其途径有两点不同:l. 徐冰造非字,心中实有字,并认为造出的字不是字。邱振中不是造字是复现,心中也认为这些是字,只是现在不是字,待考。2. 邱振中用待考文字消解字的语义功能,目的很明确,想透过笔法和平面构成提供给人们纯粹的视觉形象,即线和空间纯形式的抽象绘画。尽管徐冰的字的组成和刻制也有纯粹空间视觉形象的追求,但它更少有表现性和表情特征,它提供给人们漫长的机械的刻字过程的感受,这过程成为一种观念凝结在视觉形象中。
邱振中的作品是现代艺术,然而仍是书法,及用笔和章法都有传统规范的痕迹。在书法这一类似平衡木运动的艺术创造大地中,他走出了新花样。其意义并非在于推翻了书法本体,而在于启发了人们对它的重新认识和拓展,并为探索现代书法体系提出了某种方法论式的启示,据此,邱振中可以增衍出更为成熟而凝重的系列作品,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启示下,将会有更多的现代书法作品出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