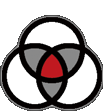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乌托邦的幻灭 |
文革后的伤感现实主义潮流
85美术运动作为中国当代美术中的第一个前卫艺术运动,并非是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1976年)时出现的。其原因一方面,社会和文化必须开放到一定程度;另一方面,旧有的强大的美学体系必须得经过一段自我的反省和清算,这个反省和清算即是本文所谈的新写实主义绘画“伤痕”与“乡土写实主义”。
毛时代之后的新现实主义艺术也并不是在他的时代结束之时(其标志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立刻出现的。在文革后的两年,1976~1978年,美术的形式和题材基本仍延续文化大革命的歌颂式的模式。歌颂领袖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老一辈革命家们。这时期对四人帮的批判是漫画式的,政治宣传方式的。
直到1979年8月连环画《枫》发表,才出现了艺术的、以现实主义手法暴露、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悲剧现实的新绘画。同时期,在四川、北京等地,一批与《枫》的题材相似的,描绘文化革命中普通人民,如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油画作品出现,这种绘画被称为“伤痕”绘画。“伤痕”是1978年8月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并立刻引起极大反响的一篇描述文革悲剧的小说。“伤痕”小说和“伤痕”绘画都是出自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一代人之手。仅管在这一代人中,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背景的不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狂热的革命造反和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上山下乡(到农村边疆接受农民、牧民的再教育)运动。在他们天真无邪的青少年时期碰到了这样不同寻常的激荡的时代,他们不但经历了狂飙般的红卫兵战斗队生活,也尝到了那似乎数十年如一日的平淡而艰苦的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精神状态既有乐观的、迷狂的投入,也有悲观的、戏剧性的悲剧体验。正是一种试图再现这种投入与体验的冲动促使这一代画家创作了“伤痕”绘画。
如果说“伤痕”绘画试图再现这一代人的“当时的纯洁、真诚、可爱和可悲,用形象和色彩,用赤裸的现实,把我们这一代最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注),那么稍后,他们转移了视角,从他们自身的悲剧转到“他者”,这他者在他们看来是“另一个”纯真的乡土世界。1980年初,以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作品为代表的“乡土写实”绘画开始流行。画中人物都是在边疆农村、异域僻壤辛苦劳作、默默生活的小人物,现在画家们用自然主义、甚至是照像写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他们的形象和“苦”、“旧”的环境。画家极力强调其纯真的特性,为此甚而不惜描绘出他们的木讷、呆滞的面孔和眼神。这里的“丑”与真和善相连,故而是美的。值得注意的是,“伤痕”和“乡土”绘画中的主要形象都是女性,因为女性代表着纯真、美和善。如《枫》中的卢丹枫,天真、可爱,在武斗失败中,不肯投降,竟死在其敌对派的头头,她一向钟情的男同学李红刚面前。而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中间着白色衬衣的女学生也是武斗的失败者,画家试图刻画出一个纯真、向往真理然而无辜遭受痛苦的女性。画家将这些女性作为这一代人的象征,以此认识和反思自己的狂热和情感,进而清算以文化革命为代表的毛式马托邦世界。
任何乌托邦世界都是宗教的,尽管它是主张无神论的。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s)认为乌托邦是“上帝死了”之后所留下的一个虚空而产生自由无神论的王国。毛泽东的乌托邦即是这样一个虚空的王国,在那里,他的异教性格和无神论创造了一种“不断革命”的神秘性,而这种神秘性又使人们忘记身边的痛苦与不完美的现实,去追逐未来一个完美的桃花源。因此它的乌托邦实际上是一种对完美的未来的畅想,总是与不完美相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毛泽东的文革美术都是在编织这样一个畅想。而天真烂漫的青少年——红卫兵则成为这个畅想曲中的一个个音符,畅想不都是和平,也有暴力与破坏,“因为必须打破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世界”。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美术和革命样板美术都是建立在这种革命乌托邦式的政治化的美学基础上。
但是,当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中的灾难性的政治现实为人民所认识后,在脱掉了美学的政治外衣后,这乌托邦美学立即显现出它的非现实和非真实性。于是建立在怀疑主义基
础上的“伤痕”绘画和“乡土写实”绘画去质疑何为“艺术的真实”即是必然的结果,艺术家试图用尽量模仿现实的手法去再现那些他们认为是“真的正在发生着的现实”,他们试图用绘画解释两个“真”,道德的真和艺术的真,其方法是用艺术的真去批判道德的不真。正如罗中立所说:“我画了一个大尺寸,是想让人们停住,去细察,去领会那虽平凡,但却惊人的细节。”“农民的喜、笑、怒、骂,农民的真、善、美,令我感到有一种没有污染的天性。他们质朴、粗俗、敦厚、平凡的性格特征,常常使我自惭形秽,我已经有点身不由己了。”
但是,任何艺术家都没有“纯真之眼”,在艺术家的视网膜和被表现的对象(人物或自然景物)之间,并非是一个直接的类似透视之类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这里存在着一个先定
及由特定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结构所约定的一道屏幕(screen),当艺术家将被表现对象置入其画面中后,这些形象已经被这屏幕所改造。因此,“伤痕”和“乡土写实”的现实主义绘画仍然是一种创造的幻觉(任何现实主义都是幻觉)。
在控诉了毛式乌托邦的灾难后(“伤痕”绘画),他们又想用另一个乌托邦世界:简朴、纯真、自然的消极乌托邦去代替破坏性的激进革命的乐观乌托邦。恰如罗中立的“父亲”以毛泽东肖像的规格、尺寸去描绘一个老农。因而当时曾有人提议将它挂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替换毛的肖像。这里于是产生了一个悖论,平凡即是平凡,一旦把它升为伟大,就失去了平凡
的存在意义。所以,当知识分子极力强调这平凡的伟大价值时,这平凡的形象和载体即成为他自身或者说社会中的某种价值取向的投射,已经不是被表现的对象本身原来的平凡与自在了。
因此,艺术家若想永远表现出这平凡和自然,就必须使自己的生活也同样平凡自然,就像陶渊明必得亲自躬耕为生,而才有其自然空灵之诗,而不是只相信一双能发现平凡的眼睛。因此,当知青画家们一旦失去了他们早期的冲动和不再与平凡的农民共同呼吸时,其作品就会失去平凡的魅力,而走向矫情,走向一种异国情调式的乡土写实,最终艺术的真实与道德
的真实也就变得苍白无力。事实上,到了80年代中期,“乡土写实”绘画已经成为过多追求精致技巧和乡土风情的异国情调式的绘画了,并与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唯美主义画风融合
为一种持续至今的学院主义画风。于是无论是先前的毛式革命乌托邦还是他们一度曾向往的桃花源式的乡土乌托邦,至此都消失殆尽。
但是,这红卫兵一代,或者说知青一代(有人也称之为第三代)画家毕竟曾真诚地批判、清算甚而反省过自身留存的文革乌托邦的虚妄,然而他们的上一代,那些曾经是五六十年代
及文化革命中毛式乌托邦艺术的真正主力创造者,在文革后则立即失去了那种原有的理想主义热情,转而提倡无主题绘画和形式美绘画。他们曾经深谙毛泽东大众艺术的创作模式,然而,一旦当他们抽去了这种艺术的精神因素以后,就只剩下那娇好、光洁的令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现在,这些画家又将这种“媚俗”的形式,赋予更为高雅的贵族式趣味。如果说在80年代初,在吴冠中发表了“论形式美”一文后,关于抽象与形式的讨论与创作上的探索尚是对文革的题材决定论的政治性绘画的反抗的话,到80年代中以后在技巧上则主要是极力模仿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在题材上则描绘淑女、裸女、村姑、田园风景这些与社会、政治无关的异国风情。这种状况,可以在目前大陆风行的写实油画中到处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媚俗到了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变而为商业媚俗的艺术。政治媚俗与商业媚俗的联手,恐怕是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所制约下的一种绝无仅有的现
象。
于是,至80年代中期,当新艺术对艺术本体的批判和对道德的批判都已进入苍白无力的阶段,加上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又重新复活了与文革美术类似的长官意志,使更年轻
的一代艺术家认识到新的艺术革命的必要性,加上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潮催化,于是’85美术运动揭竿而起了。
注:
陈宜明、刘宇廉、李斌:《关于连环画“枫”的一些想法》,《美术》1980年第1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