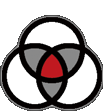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爆破与借箭:文化游击队的策略? |
高名潞(以下简称高):八十年代,你在《美术报》发表过作品,我感到你的画偏重对传统、哲学的思考,透过火药爆炸痕迹带来的神秘性与油画形象的抽象性结合起来,你一九八七年去日本后,国内许多人都不太了解你,国内艺术界对你开始关注是在日本后期以及一九九五年到美国以后,我想知道你最初从国内开始以至现在面对跨国文化问题,是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性(或当代性)的?如果你一直致力于做一个前卫艺术家,那么在中国你怎样做一个前卫艺术家?在日本做怎样的前卫艺术家?在美国又怎样做一个前卫艺术家?这里有一个连续性的传统与当代的冲突与转化问题贯穿于其中。那么在中国、日本、美国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是如何变化的?
蔡国强(以下简称蔡):在国内时,一方面我缺乏对政治环境挑战的冲动,另外也不想在旧有的观念、过去的传统表现技法上下功夫,结果两头不讨好,很不显眼。我觉得通过艺术对人生、宇宙,包括社会、文化问题进行探讨,只有当用较好的艺术手段来表现时才有说服力,也才有趣。如果忙于主张,用很多概念指导各种运动,自己的兴趣会小一些。当时在国内对西方的现代艺术也了解一些,但那些西方大师在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东西,跟我自己的现实背景距离很大。不过那些来自西方的讯息,还是间接地给我带来一个好处,使我知道现代艺术的发展拥有各种可能性。那时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青藏高原、丝绸之路旅行考察,做一些对大自然和文化传统的体验,我感觉这些普遍性的东西后来成为自己创作的基础,这样其实使我打开了时间、空间的格局,超越了当时所处的现实局限。在创作上主要是做一些个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拿画布到岩画上去拓,拓完顺着那些痕迹用火药爆炸,借一种自然的力量。再如从海边的礁石、榕树的树根拓片,然后重组形象,用大自然的力量使有限变为无限。当时所处的环境比较封闭,用火药主要有两个突破:一是我对所生活的那个时空感到压抑,用火药爆炸这种破坏性的活动,使自己获得解放,另外是在作品上火药爆炸产生的偶然效果,使我推翻了某种保守的造型惯性,通过爆炸的偶然性,产生对传统文化负面压力的突破。
高:我们可以从艺术语言的角度继续这个话题,艺术语言问题大家说了很多年,国内从八十年代就开始谈,一些人强调怎样把艺术语言弄得精通,一些人则重视用艺术表现某种精神的东西,这两个说法似乎一直是矛盾。现在看来语言问题跟用什么样的主题,用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行为、物质、媒介以及创作过程都有关系。说具体些,如你早期在画布上爆炸下痕迹,那时你考虑到突破旧有绘画语言,后来你执行一种真正爆炸,在公共场合,在天上、海上、戈壁滩或种种公共建筑物上空,这之间的转化、变化是什么?
蔡:在国内时通过爆炸,表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性。火药本身是爆燃的,而作为易燃的画布油彩在爆炸后会产生奇特的画面效果,所以它们之间是"破"与"立"的关系。去日本后,这些想法发展到室外来。我感到在大陆时主要是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理解阶段,在日本最重要的是使我注意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日本人基本上认同和我们一样的价值观,如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且将这些保留在生活里面,而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很多东西已不在日常生活之中。还有就是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新科技,譬如现代宇宙物理学。我在大地上做作品,当时主要考虑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看人类在地球上的实践活动。在大地上,在昼夜之交的黄昏里使用火光和爆炸的速度让时间、空间发生混沌的变化。
高:爆炸本身的第一基本形式是大地艺术形式,但任何这样的大地艺术都不适合艺术家自己一个人去执行,必须通过社会组织活动去实现,使其他相关的社会部门投入进去,所以它有很大的社会偶发性因素在内。因此,传统的艺术家主体、物质客体的二元对立则消失,转化到系统结构的形式中。爆炸瞬间的景象与奇观已不是一种单纯的视觉形式,乃是一种社会性的合力的物化。但是,它却提供给观赏者非功利性的联想与幻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稍后再谈。谈谈其他日本同期的作品,在日本,你把古代的船挖出来,经过分解制作成木塔或其他装置艺术品,这种既有的传统文化的积淀物,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成为历史文物,你把它挖掘出来,重新放到博物馆,是沿用了杜桑的观念,但你不像杜桑强调的仅仅提倡物品本身也可以成为艺术品,而是强调文化原初的积淀物,怎样在当代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下被再认识和再解释,通过挖掘过程,以及博物馆陈列,给人一种新的启示,在这方面,你是怎样寻找这种文物的?你是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期待?从而使你对博物馆现成品有怎样的再发现?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你是否可以结合一个具体的作品谈一谈?
蔡:挖船的事,在日本和西方都有大量评论。如果跟克里斯托夫做比较,他的主要特点是艺术是自己的,花钱找人来做,而我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多东西成为我的方法论,比如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农村包围城市"等。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努力于国际化、现代化目标。他们认为自己落后,是个危险的岛国,成为国际化、现代化的强国是他们的主要课题,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他们出现了很多反省,认为百年来国际化现代化的结果是西方化,在经济上国际化现代化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是在政治、文化上还是处在西方的边缘状态。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去的。跟六七十年代或是更早去的艺术家相比较,我去的时机好,当时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他们理想的文化英雄主义模式和对自己文化充满信心的精神。火药爆炸产生的不可预料性和对时空的另一种解释,既有东方文化的神秘与原初的内核,又跟西方当代艺术形式,如大地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等相比照并以强有力的视觉效果与之直接对话,因此在日本他们把我当做他们的课题与典型来支持,我也就可能做很多事情。我提出在一个小村庄里挖船,也可以国际化和现代化,挖那个船连结着那里的历史,从这件事去发动群众,当时好几百人来挖船,大家都是自愿的,他们把它当做自己的事来做。
高:你后来到了美国、西方欧洲一些国家,参加了不少展览,搞了些大型装置。像在古根海姆做的《成吉思汗的方舟》,还有在一九九七年威尼斯双年展,你用传统木塔改装成带有中国国旗的火箭,这些作品与日本时期的比较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有了什么新的感觉?你在选择文化资源和材料上有什么想法?
蔡:在日本时很注意风水、中药这些东西,当时感到困难的是我们可能很快可以用西方的一套方法论来表现这个世界,但很难用他们这套东西认识和思考这个世界,在表现这个世界的后面是我们如何认识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方法论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这一点我们远逊于自己的祖先?
高:你是说,你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的实践活动当中去找到某种方法论和世界观相结合的一些范例。同时,你也认为在西方现代艺术中,在方法论上有种非常大胆的,打破任何限制的自由性。你认为我们传统文化实践,如中医、风水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自由联想与融会贯通的方法论,你想把这个传统的东西转化到当代,并使东方传统和西方当代的方法论相融合,而非表面形式的嫁接。但是个人艺术创作过程中,你是如何进行这种转化的?
蔡:我一直感到我的创作活动好像钟摆的状态,一头在自已的文化主体处在新的时代所面对着它自己应有的延续发展问题,另一头是我生活、工作在西方体系内,西方文化主体的发展之课题也会成为我的课题。这两种来自于不同原点的问题意识和表现追求,有些是对立的,有些是交叉的。每一次侧重一边而形成的拉力,构成了徘徊和稳定,这种状态构成了作为东方艺术家的困惑和特点。
高:这需要艺术作出判断,即艺术品的有效性与它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处于哪种对话状态有关。作为艺术家,你得找到一个具体形象,尤其是让大家看的东西,引起大家的思考。比如说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成吉思汗的羊皮筏,你是怎么想到的?羊皮筏显然是蒙古人用来征战的工具,丰田车的发动机与羊皮筏之间什么关系?现代工业战争与古代军事战争不同的负载工具并列,是否还有它的更深层的文化、经济意义?丰田发动机代表东方日本经济占领世界市场的动力,成吉思汗的羊皮筏代表军事文化的征服传播。但所有这些意义、语义都是由具体的羊皮筏和丰田发动机表现出来的。
蔡:这个作品题目叫《龙来了!狼来了!——成吉思汗的方舟》。狼来了的故事其实是从西方来的,后来中国、全世界包括伊斯兰教国家都用这个故事。离开日本到美国对文化差异问题变得比较敏感。在纽约平时看到的大量有关中国的图片、杂志封面,主要是担心二十一世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强大,而这里他们都常常使用龙来比喻。在东方龙是作为宇宙力量、神权等正面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里龙主要是恶魔的象征。我的作品一直比较有兴趣把历史题材和当代艺术形式内容搅在一起。一九九五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马可·波罗》,是西方人到东方来,而成吉思汗是从东方到西方,征服到匈牙利直到德国边界。以前战争时最怕江河挡道,羊皮筏平时是士兵的水袋,碰到河流可用树枝摁绑为渡船或浮桥,它极为实用又非常有效率地充当东方军团征服世界的工具。在这件作品上我把它作为古代亚洲力量的象征;作为现代亚洲经济力量的象征,我选了丰田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是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出来的,省钱,省油,又快。两种古今亚洲的交通工具串起来形成一条龙的造型。从地上堆起来,观众走进去,迎面就是一个腾空来的怪物。艺术最好玩的是可以对事物处在模糊状态时的任意表现。像六七十年代高科技的发展和洪水般的物质文明将会对人类命运有否影响的论争中,就有许多艺术家做了很多这方面包括环境问题的作品。艺术家不似法官要作是非判断,我用成吉思汗的“狼来了!龙来了!”是不是站在爱国的角度,表现中国正在强大的野心,正面歌颂她呢?还是站在另外的角度去批评呢?人们尽可以去评说。艺术敏感地反映这个时代各种力量关系的变化,而它所表现的内容,或担忧、或期待、或支持、或反对都是存在。
高:《草船借箭》这个作品其实很大,也是比较新的作品。从古泉州运来的船骨,身上插上几千支羽箭,虽千疮百孔,仍然虎虎有生气,凝重而肃然。船尾插上的中国五星红旗和窗外的美国银行的美国星条旗相对应。西方媒体每次发表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时还是愿意看到“大批判”和扭曲的中国人的脸等,他们期待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草船借箭》的照片在媒体上却相对被曝光较少。《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这件作品是反西方的。我当初翻译这件作品就是直译的"草船借箭",美术馆担心西方观众不明白,加了个“借敌人的箭”,加“敌人”就敏感了。在中国,“草船借箭”的故事多被看做是一种智慧和阴阳转化的哲学的范例。现在将这一故事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好像美国和中国成了互相的敌人,所以这篇评论的角度仍是西方冷战思维的。这里我还想讲另一问题:找到一种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艺术题材,尤其进一步找到一种具体形象——如草船——来激活当代人最敏感的神经,是装置艺术的重要课题。一些人认为你们几位在西方比较成功的艺术家的作品好像是将东方传统的东西卖给西方,或者说有东方主义的倾向。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观念中的策略问题。“策略”这个词从负面角度也可以说是“机会主义”。你是在西方的美术馆搞个人展览较多的,你是怎样考虑策略问题的?
蔡:其实我不仅用中国古代的东西,有时也用比如《圣经》等异文化的东西。像今年年底要做的“做最后的晚餐”计划是:把发烟筒送给荷兰一个古城的千家万户,让人们在二十世纪最后的黄昏、烧晚饭的时间,在各自的壁炉里烧烟,让一个个已成为装饰品的烟囱又冒出烟来,让明天即可进入更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时,突然回到了十九世纪的炊烟袅袅的旧景。我经常用各种文化的东西,不仅仅是中国的。我是中国人当然不要怕用中国的东西,问题是如何用。在运用历史故事和形象时,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和当代文化问题产生碰撞的火花;二是是否能转化成当代的艺术语言。比如,“草船借箭”,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西方人也能感到箭插在船上,船有一种痛感,既是遍体鳞伤,又是硕果累累。来自任何领域的人都看得出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个作品试图表现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世界里受到冲击的痛楚,以及,也可能吸收对方的东西,使之转化为自己的武器。至于用国旗是为了使那艘船有动感,当然除中国国旗外,日本旗、美国旗都不自然。
高:还有一个跨文化的问题。现在我们回到纽约的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展。从《纽约时报》和其他报刊对该展览的评论可以看出一个转变,即以前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从适合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谈中国前卫艺术。认为它是纯粹的政治性的与官方的艺术(本身是一种期待,也是以往我们自己过分推介的问题),转向更为复杂和多层次的理解(尽管还可能是误解)。这正是此展览试图扭转的,至少这次,他极力想去真正认识你的存在。此外从另一个角度,对他们以往最推重的政治波普的作品,他们认识到那大概只是一个利用西方艺术市场使自己在中国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的代表的现象。这一点他们现在看得比以前更深一点。他们看到了中国前卫艺术中的机会主义,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机会主义都是他们创造的。中国艺术家对全球经济化(或谓现代化)的冲击的反应有多种:一是玩世不恭的自嘲、反讽社会,但又利用它致富,可称之为混世魔王,本身反而能获得相对自由;还有一种是关注于自己的国土,对干预国民性有责任感,使自己的艺术活动直接卷入大众消费、市场文化当中去,抱着积极的态度去体验、去反省、去批判,同时是与大众共呼吸的。通过这个展览,西方媒体至少注意到中国前卫艺术并非是他们简单认为的意识形态工具。相反,中国前卫艺术也在批判西方价值观的现代性及其对中国社会冲击所带来的危害性,质疑现代化。同时,对过去中国的革命传统包括毛泽东本人,中国艺术家的态度是矛盾的,它不一定是反面的批判,也不一定是正面的肯定。既爱又恨,他们能理解了这一点,也算是深入了一步。像你的《草船借箭》、洪浩以及曹涌等人的作品,尽管他们理解不深,但西方媒体感觉到其中带有明显的对西方的批判性,不可捉摸,甚至觉得有一种对西方的敌意。这也好,说明我们这些作品的含意是丰富的多层次的。
蔡:这之前从东欧、苏联,从亚洲等非西方的现代艺术在西方被欣赏,常常有两个特点:一是对自己文化、国家体制的批判,另一个是证明自己也在致力于学习、追赶和当代西方一样的艺术表现,而这个在西方已经形成的习惯,开始在变化。冷战后,对非西方文化、多元文化的热情,将难以西方的一厢情愿创造,形成一种西方不得不面临的,真正的非西方、多元的当代文化。可能有时我们看起来还像是大宴里的春卷,但春卷要是带了菌,却可以使整个美宴食不安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