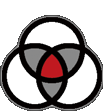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女肖像:是文化的主体,还是文化的“宠物”? |
陶咏白
画概念的界定,因各家的着眼点不同,其说法也不同。有依据真实具体的人造像的艺术,称之为肖像画;也有的不管所画之像主是“肖似”还是“神似”,只要有像主在画面上签字确认,就可称其为肖像画。而那些并无特定像主的肖像图式,有论家称其为“类肖像”;对那些借人物来作为形式表现之依托的人物画,就称它为“准肖像”。在西方其肖像画的概念更宽泛,发展到有表现性的肖像画、观念性的肖像画、抽象性的肖像画等等,不知与像主还有多少相像之处。从这些五花八门的肖像画品种来看,不外乎肖像画的内涵与外延之别,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换个立场来看肖像画——即以女性文化具体到女性艺术批评的角度来审视肖像画,那么又可得到全新的视野。
女性文化作为文化之范畴,它本身具有双重性,它是总体文化的社会存在,既是总体文化的成员,又有它自己特有的领地。英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埃德纹?阿登那和秀莉.阿登那夫妇认为:在男权文化体系中女人构成了一个“失声的集团”,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与(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相重合,却又不被其完全包容。这两个集团尤如两个互相交错的圆,失声集团的圆,大部分与主宰集团的圆相重合,但其中一部分是溢出重合区域的月牙形,处在主宰集团的边缘以外,称之为“野地”。这是女性独有的领地,是属于女性无意识感知经验的领域,这是不能用男性的主宰集团所控制的语言可以表达的,因而这部分“失声集团”的女人空间,是块“野地”。
这块野地,是女人共同的经验和感受,形成了女性超越时空的“集体经验”,这是在历来女性的道德行为规范、女性的价值观念,以及女性对于人际关系和交流方式等的基础上凝聚起来的“集体经验”。对于这部分的“文化”,如法国杰出的存在主义思想家西蒙?波娃所说:“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有意对这一领域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思考的能力。这一领域就是女性的生活经验。”基于女性的“集体经验”,由同一性别构成了同质的意识,所以称其为女性意识。
这是外在于男性情感、感受、意识而形成的女性文本。这种同质意识便是女性独有和共有的女性意识,它涵盖着女性对历史的反思,对命运的反思,对价值的自省以及内在体验,审美活动等一系列的自我感觉,认识评价。女性艺术批评正是以这块“野地”作为出发点,这也就与传统的男性文化批评有不尽相同之处。由此对于同一幅作品也就有了与传统的男性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甚至是相逆的批评,这在西方的女性批评中比比皆是。近年由美国的两位女艺术史家诺玛?布罗德(Norm3 Broude)和玛丽?葛拉德(Maryd Garrarl)编著的论文集《女性主义和艺术历史》中,以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对文艺复兴至20世纪后期的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绘画经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该书的导论中指出,她们所强调的是“关于性别偏见,对于每个时期的西方美术所产生的曲解”,是“对世界上的价值、种类与观念结构作一番新的调整”。
她们认为,中世纪美术作品中夏娃与圣母玛利亚是两种极端的形象,同属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显然与人世间现实中的女性是难以沟通的。到了18、19世纪,法国绘画作品中的“幸福的母亲”和英国绘画作品中“破灭的女人”又成了两个对立的主题,但又都是为完善布尔乔亚家庭的尊严而服务的,依然只能代表部分女性的生存状态。总之,这些形象不能真正反映当时女性对自我形象的追求。她们对大师们的名作也颇有微词,耶尔?伊文对佛罗伦萨广场上一些备受赞赏的名家雕塑群指出,这是一个宣传父权的政治性雕塑的展示区,其中所表现的英雄故事,正是宣扬着男性对女性情欲的驾驭和征服。萝挪.高芬认为,提香作品中的女人,充满了令人无法拒绝的色情魅力,他是以性欲来界定人性,而女性只是男性的玩物。玛格丽特 ‘卡罗认为,鲁本斯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于强暴题材的热衷,而这种性暴力,表现出男性对女性的权力支配。
泰玛.加柏说,雷诺阿尽管被塑造为纯粹的画家,其实他是个专画女人的画家。他赋予女人一种感官的享受,所以还有人说他“用他的阴茎”作画。他的画笔,是一个充满肉体乐趣的器官,从而唤醒了感觉生命。似乎绘画行动是男性的,文化也是男性的,而“女人”只是文化以外的肉体,是自然的延生物,作为文化主体的身份也就被注销,她们对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一画也提出不同于所谓“有伤风化”的批评,她们认为,在同一画面中,男人衣着华贵而女人却一丝不挂,也意味着男人是文化的代表,而女人是自然的象征。
总之女性在男人眼中,典雅的缪斯女神是为了向男人提供灵感,而一丝不挂的卖春妇是为了娱悦男人的感官,这两类形象都反映了男人的性支配观念。因而,为了反其道而行之,美国的《女士》杂志刊登了一幅新的《草地上的午餐》,草地上是两位衣着华丽的女子,在她们身旁是一个弯腰弓背的裸体男子。在这幅画中将传统绘画中女性的角色转嫁给了男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的美术史家卡罗?邓肯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内的骚娘们》一文中分析毕加索、马蒂斯、雷捷、杜象、塞维里尼、德库宁等现代画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时指出,如果20世纪的现代艺术,是关于形式的推进,那么,在所见所闻的现代艺术史上,为什么却满载着各种各样女人的形象?描写女人的身体或身体的局部,除身体的构造以外,绝无身份可言。
她们不是坐着的女人,就是斜卧的裸女,不然就是下流女人。为什么艺术史对这种身份低下并可以出卖肉体的女人特别钟情?这说明在他们的笔下都在强调男性的力量和优越感,而将女性还原为纯粹的动物式的肉体,全然无视女性的人类属性。可见女性在传统的艺术史中是个道具,是个文化的“宠物”,而不是文化的主体。诚然,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并无意贬低毕加索等大师,而只是想将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手段,对以男性为本位的艺术史和性观念进行反驳,以实现一种超脱了性的男女共生的新的观念。这无疑是以一种新的艺术批评的视角,揭示了以往学术研究中被男性所“失去了思考能力”的偏向,这是“失声集团”为自己开辟了一方新的批评领域。这块领域被西方女性主义者开垦了近20年。
早在1971年美国的美术史家琳达?诺克琳发表了《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一文,从而开创了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的先河,也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20年来经美国的诺玛?布罗德、玛利?葛拉德,英国的罗西卡?帕卡、罗里塞达?勃罗克及泰玛.力口柏等等艺术史家的研究,推进着女性主义艺术史或后现代女性艺术史的建立。在中国这还是一方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我们无意去照搬西方的理论来对照自己,但我们稍为留意,女性在艺术中是人还是“物”的属性,却让你触目惊心地感知到问题的严重性。
就拿肖像画来看,且抛开肖像画或类肖像、准肖像等纠缠不清的概念,就以女肖像而言,古代专有仕女画,民国初有月份牌美人画,二三十年代封面女郎盛极一时,50年代后沉寂下来,而80年代随着商业浪潮袭来,风情万种的青春靓女、娇艳妩媚的时尚女郎,充塞着广告、封面、电视及画展等传媒,女肖像成了当今传媒的时尚,女性形象如此受宠,这是祸还是福?透过这些女性形象的表层,到底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文化?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女肖像,是文化的主体,还是文化的“宠物”?把女性看做人来表现,还是当作“物”来表现,这是有着原则的不同的,当传媒所传递的不再是女性的自尊、自爱的形象时,女性也就只能是供人观赏、取乐的“宠物”了。
1995年世妇会期间,在中国美术馆同时有两个油画女肖像圆展,很能说明些问题。一个是在小展览室的女画家王海燕的作品展,她画的都是当今对人类卓有贡献的女人肖像,如世妇会的秘书长蒙盖拉夫人、前苏联女宇航员斯特拉日娃、美国著名女摄影家玛瑞‘爱伦马克、中国核物学家吴健雄、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妇联主席陈慕华等中外杰出的女人。
这些肖像无不显示出她们自尊而又自强,充实而又坚毅,平易而又高尚的人格精神和性格特征。而另一位男士在大展厅所展出的系列女肖像,从古装仕女到现代女郎,却一色的是些矫揉作态,迷惘空虚的病弱形象。女人在他的固中只能是弱者,是“花瓶”,是“宠物”,是个依附者。这充分流露出当代一些男士对旧式女性的怀念,反映出男性文化本位的欣赏趣味。这两个画展,反映出了男女画家在思想、情感、感受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倾向,在审美价值观上存在着极大的反差。
是把女性当作文化的“主体”,还是当作文化的“宠物”来表现?在一般男性的眼中女性形象仅是文化的“宠物”,当他们在现实生活的争斗中拼搏得身心疲惫时,就需要温柔、贤淑的女性来抚慰焦躁的心灵;当他们欲念需要时,他们又喜欢那形骸淫荡性感的女性来取悦。因而在这些女性形象的背后,是男性自我观照也是我们窥探男性心理的一面镜子。而一般女画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女性关照自身的生存状态、生命价值的写照,是作为女性自尊、自爱、自强的文化主体来表现,这同样也是她们心灵的一面镜子。
例如曾蜚声二三十年代的女画家潘玉良,当今人们感兴趣的是她曾为妓为妾的传奇色彩的身世,但对她的艺术不甚了了。她是我国早期西画运动中杰出的女画家,她1921年就留学法国,对油画、雕塑、版画、中国水墨画均有很深的造诣,尤精于油画。她以女性对色彩特有的敏感,深得印象派色彩的奥妙,在我国早期油画普遍还缺少色彩感的时期,她被时人称赞为“中国印象派第一人”。尤其是她的系列自画像,画中人哀怨、悲愤、刚强、坚毅的神情,充分表现出她在与命运抗争中桀骜不驯的性格和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她在20年代画的《假面具》、《歌罢》、《落寞》,都流露出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的悲情。她有一幅《我的家庭》,是她的家庭成员的肖像组画,这种形式在中国油画肖像画中实属罕见,而这幅画也充分表达了画家特有的人生经历,从而才有对美好家庭生活热切的渴望和十分珍惜的情感经历。
另一位于1924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周丽华,30年代她曾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时人对其艺术上有“新的形式”,有“优美的线条,温丽的色彩,深刻感人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她有幅题为《嫠妇》的女肖像画,画中人神情哀怨、苦恼,环绕肖像还有父母、公婆、妯娌、叔伯、乡邻等表情各异的头像,象征着宗法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画家采用像电影化进化出的手法,也可说是种“意识流”的手法,增强了画面压抑的气氛,她似乎被无形的网所笼罩,挤压逼迫得喘不过气来,画面很有感染力。这是作为女性的画家对女性命运有着特有的感受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她的另一幅作品《永别》,画中是一位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十字架形的造型弥漫着悲怆动人的情感。而蔡威廉的一幅《女肖像》,背景用了一圈圈光环,这或许是女画家对画中人有像圣母玛利亚似的圣洁、善良的歌颂,或许是女画家对人格精神的追求。
60年代,赵友萍的《女代表》是画西藏翻身农奴中的女性形象,女人作为真正的主人,走上了政治舞台时所流露出的那种神圣庄严的心态,又掩饰不住激动而有些胆怯的复杂心情。温葆的《四个姑娘》则真实地描绘出4个性格各异的农村女青年质朴的本性,她们充满青春活力,憧憬着美好未来,表现出当时农村新一代女性的形象。王霞的《海岛女民兵》则把当时女性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表现得十分到位。
80年代吴海鹰的《红花冈的怀念》是陈铁军女烈士的肖像,画家仅用红、黑、白单纯的色彩,稳定的三角形造型,画面饱满,浑厚而具力度,很恰当地表现出烈士性格内向、沉静、执著的特征,没有故作昂扬的姿态。画风的单纯朴素,一如主人公沉静、自信的心境。男画家也画女英雄,在他们笔下的女英雄,往往是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概念化的人物,或者就是高洁得如同圣女。如画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在闻立鹏笔下,把张志新放在高山上,身穿洁白的衣裙。躺卧在血泊中。画面形象固然给人崇高感,但又多少带有对本是弱者的女性的同情与惋惜。
虽也作为文化主体来表现的,但在男女画家笔下潜藏着不同的审美价值观,男画家笔下是对他者的描绘,而女画家笔下是对自身价值的确认。男画家笔下的女形象往往附丽着他们的审美理想,如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是他对古典理性美的追求,而刘秉江的《塔吉克新娘》是他对装饰美的追求。“新娘”在他们的笔下,实质上是作为他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形式探索的依托。
而出现在女画家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她们是些真实具体的人,是对女性自身的生存状态、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表现,这是些具有时代特色、个性特色和女性意识的形象,这是女性发现自身,确认自身价值,作为文化主体进入审美文化的领域,从而确立了女性绘画的美学价值。
诚然,女性艺术批评无意去反叛传统的艺术批评模式,她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风景”,摆脱习以为常看问题的框框,从“野地”上找出那“失声”的语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