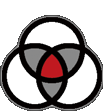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轻舟已过万重山——苏笑柏的“回乡”路 |
轻舟已过万重山
——苏笑柏的“回乡”路
陶咏白
苏笑柏的名字,在人们记忆中已淡忘,但一提起22年前六届美展上的一幅油画《大娘家》,却又可清晰地跳入脑海,这幅画的魅力是永在的。我曾在《画刊》的前身《江苏画刊》1985年6期上发表了题为《柳暗花明处——评苏笑柏的油画》一文,人们对他那时期的作品有个较全面的了解。此后他从金银手饰工厂调进湖北美术院成为专职画家,接着又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系研修班学习,87年他获德国文化艺术奖学金,到杜多尔多夫国立艺术学院读研究生,自此苏笑柏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2003年,在中国北京国际双年展中才见到他的两幅抽象画。离那《大娘家》,离研修班结业时的《飞天》,离人们所熟悉的苏笑柏特有的油画语言“稻草黃”时期已远去了。
笔者有幸参加了他于1993年策划的中德艺术家交流互访活动,在德国他的工作室看到他走出国门后四、五年的作品。墻上还挂着不少以往熟悉的农舍、土墻、小院,散发着淡淡的乡愁,画案上有他的几本水墨册页,那每一页上就画一把绢扇,或一张明式木椅、一台老式橱柜、一个铜烛台……,细细的线,淡淡的色,在朦朦胧胧的墨晕中透着怀旧的感伤。全然没有了他在国内时那绚丽而又洒脱的油画中所传递出意气风发的精气神。这是身处异国的情感使然,还是艺术生存的策略?同往的王怀庆、艾轩曾有在异国游学的经历,都为笑柏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坚持在异国他乡发展而佩服不已。艾轩甚至说:“若让我这么生活下去,非憋死不可。”但笑柏执意在异国打天下。据说不久他在德国西部边界建立了一个艺术交流中心,室内布置着中式木结构家俱,立着他的水墨柱的装置,室外有从国内移植去的具有活化石之称的银杏树,甚至还背去了他曾工作过的铜厂的大铜锣。他精心营造着一个中国“家园”,在那里不仅接待着来自各国的外国朋友,也接待了不少的国内画家。
98年,他转送来了一本画册,看到他用油画语言所画的古旧屏风、明式太师椅、老式的画案等“文物”,较之他那感伤的水墨画似多了些热情,但在不少斑斓、响亮的色彩背后仍隐藏着一颗孤寂的心灵在游荡。所好的是他的作品倒为一些外国陈列馆和收藏家们所青睐,得到他们“持续而有规律的收藏”。他难道就此不断地制造中国“文物”,去获取在西方艺术界的位置?事过5年,他参加北京双年展的作品——《网状回忆》,全然找不到中国的“文物”符号了,以一种国际性的抽象语言,消解了具体形象,只有红、黑、黃(其实就是那“稻草黃”)为主的色块变奏着他的思絮、情愫和想象。放弃驾轻就熟的艺术语言而选择别样的语言,对苏笑柏来说无疑是一种冒险。他说:“我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只是一种装饰,一种挂在墻上的好看的东西,成为起居室的点缀。”“我真的不願意因为非常民族性才被看成是世界性的了。我希望自己的绘画作品有绘画本质意义上的原创性。”苏笑柏看透了西方人士对“文物系列”的青睐,只是因不同文化的别样而新奇,停留在一种猎奇式的浅层次审美上。如何让自己溶入世界文化艺术发展的主潮中,又不失个人独特艺术的原创性,这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他毅然地放弃标志中国式的文化符号,大跨步地走向世界性的抽象绘画语言领域中去比试自己的能耐。这意味着他首先要摆脱以往在国内给他带来荣耀的素描、色彩、造型等等绘画理念和绘画经验,这对一个成熟的画家无论如何是一种痛苦的经历。然而他义无返顾地忍痛割爱,舍去“符号化”走向抽象绘画的领域。绘画观念转换后的新艺术让人感到陌生,也失去了一些收藏率,但有识之士发现,“苏笑柏和我们开了个大玩笑!”虽然他画面的形象变了,但骨子里还是苏笑柏。那种热烈中的沉稳,明快中内敛的色彩情调,只有这位中国男子才具有的艺术气质和性格。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从具象向抽象转换的绘画,丢失了独特的文化符号的依托,要在世界众多的抽象绘画中突现出自己的风格,在绘画手段穷尽的当代,要创造出原创性艺术,还是个有待探讨的课题。他在困惑中如何寻找到那独一无二的“自我”呢?
此后两、三年,他一头扎进福建去“玩”大漆了。这位曾经学工艺美术出身的画家,尤其是到了德国,据说,那里的绘画材料,总有成千成万样的品种让你挑选,并且还日新月异地在更新。生活在这个对绘画媒材的追求无以伦比的精细、无以复加的精美挑剔的国度,无疑激发着他对绘画材料研究的兴趣。听说福建有用大漆做家俱、做磨漆画的工厂。他原本酷爱木工活,在他德国“林摘安”工作室就置办了一套先进的木工机器,也自然对这种有着二千多年民族传统的纯天然的大漆工艺有兴趣了,当然他不是去做我们所熟知的磨漆画,他的兴趣在于用大漆这个材料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绘画媒材。列时几年的试验,他终于成功了,这种用大漆浸透麻布,绷在画框上制成的画幅,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苏氏漆胶画。他以全新的观念和制作工艺使古老的漆艺唤发了新的生命,并为绘画增添了新媒材。大漆以棕红为基本色,他用矿物颜料调制出了丰富多彩的色域和色层,单就一种红色他竟有深红、浅红、鲜红、宝石红、女儿红、状元红、腰果红、腥红、铁红、银珠红、鸡血红、鎘红、金桔红、银桔红,还有中国红、英国红、威尼斯红等等名堂,我真不知他对一个“红”怎么会分辨得如此精当细微,竟可把千年来这种单调的涂料,调制出如此丰富多彩的色彩语言,用得象油画颜料那样随心所欲,一改我们对大漆的认知。大漆与麻、皮、藤等粗纤维的胶合所产生出的肌理效果也是一般绘画所难企及的。漆的细腻平整和麻、藤等的粗砺,在物质性能对抗中呈现出了内在的张力,它们胶粘成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的色彩颗粒或长短粗细别样,橫竖弯曲各异的线条,它们似一种生命的原素,在平整的流动的漆面上欢腾雀跃,闪烁着颜色的光彩魅力;那毛毛渣渣的边缘线分割着、守护着自己的领域,伸展着、游动着,迸发出活泼的生命气息。虽然它们只是形态各异,简洁明了的几何形块面的组合,并无着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你却感受到其中有的似火山溶岩漫溢的炽烈,也有“黑入太玄”神秘的黑洞,有春意萌动的田野,有万倾波涛的海洋……,他创造出了一个如此缤纷灿烂、活色生香的艺术园地,一个让精神自由飞翔的天地。他不再需要什么说明性的符号,只专注于绘画的营造,让自己丰沛思想,饱满的情感,贯注于画面空间,簇拥着色彩在火与冰的撞击中迸发出星光灿烂,把控着漆面上的颗粒与线条在无序和有序的穿梭中奏响美妙的音乐旋律,让思想的灵光在画面的随机应变中自由地欢唱。他就象一位高明的导演,让画面充满戏剧性的冲突,让绘画本身焕发出了生命的美感。他曾坦言: “以前的绘画作品中的疲软、甜美、言说性、地域性。”困扰着自己举步维艰,而他的新艺术,给自已的创作带来了无限自由的表现空间。苏笑柏以他艺术的新观念,驾驭着古老而质朴的媒材完成了一次绘画语言的革命,他终于以“独一无二”的原创艺术,得到大家的认同。固然,他所用媒材在世界上是首创,其表现手法与表现形式也与中国前辈赵无极、朱德群们所不同,他们都以中国的书法入画,以书写的抒情性豋上了世界著名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大家的行列。如今,国内的抽象画家也基本上都走这条书写性的抽象之路,或许中国人自幼就受着中国书法的薫陶,从草书发展为抽象画是天经地义合逻辑的选择。而苏笑柏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他以理性构成走进冷抽象的行列,以“极简主义”的手法,用看似全画周正、做工讲究单纯明了的几块几何形体,却又有如此丰富饱满的色彩张力,从中透出雄强、强烈而凝重的份量感,迸发出了热烈、野性、浪漫的生命情调,震憾着你,感动着你,你不觉得其中有某种你熟悉的东西在牵动着你的某根神经,激活着某种情感?你从那些看似硬边的冷抽象画面,似乎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某种基因。也难怪,自幼生活在湖北的苏笑柏,荆楚文化中的雄浑之气,鬼魅之神秘,楚魂的热烈,楚风的浪漫,早已浸润着他的心灵,溶入他的血脉,成为他的性格,他的气质,他的精神。他为人处事常常让人感到“湖北佬”热辣、强悍而执著的性格,又不乏那温情与深沉、真诚与浪漫的品性。因而他在用漆与麻、藤的胶合中,以红、黑色为主调变奏出的多姿多彩的作品中,那漆的凝重,麻的质朴中,透出一种典雅的高贵气质与粗砺的村野气息。这两股气息交融成凝重、浑厚、深沉、热烈、浪漫、大气而辉煌的审美品格。
在这种物质性组合的作品中,让人奇怪的是这一切与苏的性格、气质有着某种巧妙地契合。这难道是偶然的巧遇?不可否认,飘游国外20余年,虽已入了德藉的苏笑柏,他骨子里流淌的依然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他虽然在作品中执意摆脱了中国文化符号,但当他在完成自己独创性艺术的同时民族文化的记忆已在他意识深层构建起了他那独创的基石。虽然他在理性地设计着色块的分割、比例、铺排,然而,他与冷抽象的鼻祖蒙德里安不同,他讲究色域的交汇与相融,色相的冷暖与渐次流动、变化。他的画面色彩极具感性,单一个“红色”,有的红色,可以让你热情奔放;有的红,显得羞涩腼腆;有的红,阳光灿烂;有的红,娇艳妖饶;有的红,辉煌壮丽;有的红,也让你徒感悲伤。就那么一个“红”,却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人性化情怀。更何况那似被尘埃和烟薰的几个板块画面,不就是古代遗留下记载荣耀的牌匾?那被称为《书法》的系列,红色底版上竖式排列的一行行形态各异的小空洞,不正是飘逸灵动的汉字?被称为《纪念碑》的作品,兰色为底版的中间还带有一抹红色的灰色块,人们不难从中感到那是耸立兰天的大理石碑,碑身还飘扬着一角红旗呢。以及他称为《出版记录》、《投亲靠友》、《设身处地》……等画,虽然都是色块,却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记忆,这些色块所传递的情感、情绪、情愫、情调,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记忆的人所独具的资本。因而他所厌恶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论述,应该理解为对那些依靠民族性文化符号,或一些靠说明性图解的作品,是肤浅的艺术,而苏笑柏站在世界艺术发展的潮流制高点来审视,回望本土,吸取滋养,把非具象纯形式的审美世界从世俗的现实世界中提炼出来,清除了原先支撑艺术的意识形态内容,取而代之的是艺术本体的自身价值。这也就成为在不同历史、文化、信仰和制度背景中的人们可以共享的艺术。
苏笑柏在跨越国界、跨越民族的局限,走向世界的路程中,走过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又历经峽谷险滩行行重行行的追寻,其实是走在“回家”的路上,终于“轻舟已过万重山”,走进艺术“本我”的村子,在世界多元的文化语景中,它是独特的,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
2007年1月11日修改 方庄-芳星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