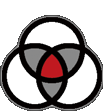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归去来兮——张红年的艺术人生 |
归去来兮
——张红年的艺术人生
陶咏白
张红年,对于80后出生的新一代人来说只是一个符号,而对于经历过“文革”年代风雨的人们,张红年的名字是有质感的,他的油画《我们那时正年轻》、《在命运的列车上》曾牵动了多少人的心!20多年前他去了美国,人们惋惜他的出走。如今,他带着他的艺术作品集回来探亲了,他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答案?
画坛新锐
美藉华人画家张红年,曾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活跃于画坛的新星。在中国新时期的美术史上,他是位不可忽略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以敏锐的思想,深切的人文关怀,高昂的英雄情结,使画作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他又能在油画语言的探索中不断出新,成为当时艺术新潮流中的先锋。
张红年的名字,是与他的油画《发人深思》(原名《不!》)、《我们那时正年轻》、《在命运的列车上》等为人们所熟知、所追捧。在他的作品里,没按通常“瞬间”定格画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手法来表现主题,而是把自己对社会问题思考过程中在脑海中闪现出的原始的流动的视觉形象,一古脑儿搬上了画布。这些零散的情节不拘时间、空间,似电影多镜头重叠组成了连续性的画面。不仅扩展了画面空间,更增强了画面的深度和广度。他的这种表现手法当时被称为“意识流”。张红年用自己独到的绘画语言,把一个动乱年代中一代人对共同命运的思考呈现于画面,让观众在多瞬间,多视点,多空间的画面中共同去体验、去经历、去回忆那段迷惘、失落、无奈…不堪回首的往事。有观众来信说:“在你的画前,我流下了热泪,我的泪决不是因为我受过苦,被迷人的英雄主义欺骗过,而是因为我们那时正年轻。”这一代人的青春,是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而显得沉重,而历史的前进,也是以这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的。他的作品也成为这个时代标记性的图象。
张红年并非停留在伤痕的悲情中。1982背起画箱,游走在母亲河——黄河岸边。他说:“我就象没见过亲娘的孩子,既激动又辛酸。”以往作画,都是领导出题目,画家再用生活去套,难免不公式化、概念化。他的《啊,黄河》把他的真实感受,以超越时空概念的画面,把缅怀祖先,保卫黄河及建设黄河,这样一个气势磅礴上下几千年的历史,纵横数万里的地域,揉为一体,画面恢宏深远具有史诗般的魅力。而他的《山乡吟——故乡月、杏儿歌、峡谷风》三部曲、《大地的馈赠》、《大地的深情》等组画,在“意识流”的多视角、多空间的画面结构中,采用河北蔚县民间剪纸鲜亮、明丽的色彩,开拓着艺术民歌风的新形式。新时期之初,他是一位在艺术上不断定出新,勇于探索的画坛新锐。
然而,1983年一次赴藏写生的行程,改变了他艺术探索的规迹,在广袤、无垠的雪原高山下,在空旷、寂寥的蓝天白云间,时间失去了意义,在大自然中,人那“诗意的栖居”,是多么自在和美丽。这不就是古人追求的那“天人合一”的大美境界!他被震憾了。这里每一个角落、每一方土地,每一位人物、每一件服饰、每一组动作、每一种场景,都具画意,是那么直观和单纯,其本身就具有绘画形式的美感。他感到以往拼命地追求新颖独到的绘画语言的种种尝试,显得多么娇情,多么别扭,多么累。从此他开始回到绘画的本源舍弃文学性的拐杖,舍弃“意识流”或民歌风的形式的探索,从绘画的“视触觉”着手,追求绘画本身的存在价值。他回到写实绘画的起点,重新迈步。1984年的全国第六届美展上,他的一幅获铜奖的具象作品《准备冬草》,其细腻却疏松的笔致是如此灵动,那素雅而饱满的灰调如此优美,令人惊叹不已。人们纳闷,在艺术勇往直前不断创新的张红年,怎么又回到了现实主义写实的原路?
闯荡海外
1984年他考入中央美院油画系攻读研究生。艺术正处于喷涌勃发的高峰期的他,1985年又匆匆出国,进入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艺术系深造,跟着洋老师学起抽象艺术来了。为了生存,他依旧画着具象的西藏题材《生于斯,长于斯》、《中午的梦》等,也许更是一种感情的需要,西藏悠远、辽阔、寂静的景象,与他在异国的寂寞孤独的心灵相吻合。他孤身一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闯荡,举步维艰。所好他的艺术被一个曾是萨金特创建的“大中央画廊”所接纳,在这个西方世界顶级的画廊展出作品,并获得成功,从此他的作品,不断有画廊展出,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不料他的爱妻,一位聪慧极有才华的艺术家,不幸罹病去世,期待团圆的美好愿望随之破灭,他的精神近乎崩溃。但他不甘心放弃美国这世界性的艺术大舞台,他得拼下去。于是背着已获绿卡却未能赴美的亡妻骨灰牵着年仅10岁的小女儿又回到美国。为了摆脱新移民的怯弱和惯性,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带着女儿搬到远离唐人区的乡村小镇生活下来。他决心要直接走进美国人的生活中,让自己的艺术融入美国文化中。
美国虽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对于美国人来说,美藉华人画家——张红年们的作品,依然是“他者”,他们只是以猎奇的心理欣赏着异国风情,并不认为这是美国的文化。在美国已生活了六、七年的张红年,深感这样画下去永远是美国的边缘文化而进不了美国的文化主流中。作为一个新移民,他从美国三百年的移民史着手研究美国的文化渊源和民风习俗,画了一批画。如果说此前的作品,他是以一个华人画家的文化身份,延续着国内开始的西藏题材的描绘,在美国创造着良好的市场效应的话。那么,1992年后推出的系列画美国的作品,可以说是融入美国文化战略步骤的实施。他画移民题材的《新家》,画美国的《万圣节》的节日狂欢、画《工会公园》中的美国人的假日休闲生活……,直至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他画女神在废墟上哀悼的《零爆点》,据悉,这幅画是最早对此事件作出反映的画作,被印刷出版,还被不知名的人士张贴到世贸大厦的废墟边来祭奠死难者。在美国人惊魂未定的时候,只有一个中国画家,以他敏感、敏锐,敏捷地作出反应,画出了具有历史性的画作。这或许是在国内早就练就的一套及时反应生活的创作潜质。他从大场景、多人物的美国的风俗或美国的历史或现实生活题材,到被他视为“养眼”(为了眼睛对色彩的敏感性)的美国的风景、静物、人物等作品,无一不表明他这位新移民,是美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他的这些作品展出时,也赢得了美国百姓排队观赏的盛况并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求学者。同时,他也得到了一位美丽温柔的美国女画家露易斯乌丽的爱情,组成了一个幸福的新家。
这一段时期他的创作是自由自在的,涉及的题材多种多样,绘画技艺的熟练,使他随心所欲地把控着画面的完美,画什么变得不那么重要,而热衷于发掘艺术的内质是他所追求的至爱。他忘情地琢磨画面的效果和笔墨的品味,追求艺术本身独立的审美价值,让艺术进入至善臻美的境界。他也被聘任于纽约艺术学院执教。
魂系华夏
张红年绘画上的成就,获得了具有百年历史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青睐,1997年杂志社请他创作一批中国历史画。真是天赐良机,多年的电影梦,多年对苏里柯夫历史画大制作的心仪,如今,终于有了可以一试身手的机会。
他年轻时特别迷恋电影,美院附中毕业后,一心想搞电影,命运却安排他当了专职画家,虽他也一直与电影和电影人有些接触。为《双雄会》画过油画片头、片尾。到美国后搞过一个电影脚本,还给《西洋镜》电影当过色彩顾问。但这都是打的“擦边球”。独立制作巨幅历史画,就象由自己导演一出历史剧让他激奋不已。他甚至有种“一吐为快”的心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表面、太肤浅了,他们只知道希腊、罗马,甚至埃及,就是不知道中华!或只是从某些电影上看到拖着辫子的男人、或裹着小脚的女人。似乎中国人就是这么愚昧、落后。他们哪里知道五千辉煌的中国文化!
“国家地理”杂志要求他能否画几幅有关商代的画。他脱口而出《酒池肉林》,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商代,是多么遥远的古代,而《酒池肉林》又多么陌生的一个题目。他何以如此敏捷,如此自信?
他从小就爱读中国古代历史,对演义、传说中的故事想入非非,崇拜武松、杨家将、岳飞、赵云等英雄好汉。对世界历史也有兴趣,古罗马革命、刚果政变等等,都会让他热血沸腾。对于创作历史画,他胸有成竹。那么,他何以首选《酒池肉林》题目作画?也许,他想到西方人把古罗马的文明奉为至高无上的神灵,而同时期的中国商周奴隶制社会,这是一个以青铜器发达为标记的时代,可以与古罗马相媲美的三千多年前古中国的文明。接着他又画了《最后的祭拜》(三星堆),着力宣扬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妇好征战》,宣扬在中国商代有一位皇后又是女将军叫妇好的伟大女性。历时两年完成的这三幅以三千多年前的商周青铜器为标识的作品,被“国家地理”杂志社全部收藏陈列,通过十几种文字遍布世界。初次尝试的成功,他信心倍增,也不断有藏家签约,请他画秦、汉、明、唐各朝代的历史画。他几乎成为在美国创作中国历史画的“专业户”,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文化大使”!岂不是对他的画最高奖赏。
他所选择的历史画题材中没有避开《酒池肉林》、《焚书坑儒》这些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前者是商周时代,贵族的穷奢极欲;后者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这本是中国历史上的疮疤,他也不管这是“家丑”不可外扬,依然以“匹夫有职”的担当,没有忘“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古训,但愿画起到警世作用。他更多的作品是弘扬祖国灿烂的文化文明。《张骞归来》、《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敦煌,供养人肖像》、《飞天》等作品,除了宣扬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庞大壮观得象海上的陆地;丝路上的一个小镇如“世贸会”那么繁华;而敦煌的石窟艺术美奂美仑、美不胜数,让你留恋忘返……。在他竭尽华丽之笔,勾勒出如此悠久悠长,如此光辉灿烂,如此震摄人心的中华文明图象中,贯穿着一条主线: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广交天下朋友,谋求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泱泱大国。
张红年十年来创作历史画的热情一发不可收,他甚至感到画的场面越大、人越多、越复杂,才叫过瘾。因为,他并非只是为画而画,他把作画的过程中当作课题研究的过程。也使我们感到了张红年历史画与以往我们所熟悉的模式有所区别:
人性美——爱的主旋律。我们看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画,而张红年在画作中追求着人性的光芒,即使在残酷《焚书坑儒》中,他并不张扬暴力的残忍,更重着于遭难的儒生与家人、亲朋、学生之间亲情、友情、爱情在生死决别时的悲情,悲剧在爱的旋律中奏出人性美的主调。《妇好征战》中,把原是残酷的战争场面处理成兄弟相残的“安魂曲”,暧灰的调子,象陈旧退色的照片,似乎沙场的撕杀声已远去,空留一片黄土地,让人在惆怅中反思。而《张骞归来》、《郑和下西洋》更是高扬着国际主义精神,“四海皆兄弟”让世界充满爱的主旋律。
抽象构造——平面上的戏剧大舞台。他的历史画,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他不用“瞬间”和焦点透视的老章法,也没用以往的“意识流”的手法,如何在平面的画布上有序合理地把众多的人物安排在大场景的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情节中?从洋老师那里学到的抽象绘画原理,使他在宏阔的画面图形设计上变化迭出富有生气,在空间层次的推、拉中运转自由,他把人物、情节安排在运动线的律动中拉开“舞台”戏剧性冲突的帷幕。人们不难发现,他善于运用光和色块来组织画面起伏运动前行的运动线,而这束光,并没有固定的光源,应画面运动所需而设定,《敦煌——供养人肖像》较突出地表达这种理念,画正中是著红衣的女供养人,左上角的烛光从身后照来,照到地下的画纸,而从远处门洞里照进来的自然光经过长长的画廊和众多的人物直照到画师肩上。在烛的暖光和自然的冷光相交替中画面出现了两个空间,站在这空间的交叉处的供养人在冷暖光的衬托中显得格外地美丽动人。在他那些宽银幕似的画幅中人们不难发现光带象“一条游走的龙”扭动着、腾越着向前。他以抽象的构成驾驶着写实的绘画,在多视点、多空间繁复而有序中奏出饱满、丰富、浑厚、深沉的交响乐的气度和力度。其间既有“命运交响乐”,也有“欢乐颂”。
色彩的魔术——二种对比色的奥妙。他的历史画大多是2-3米宽之间的大尺幅,但画面色彩干净、利落,透明、鲜亮,这是积15年的对比色研究,摸索出的一套色彩规律。他画一幅画,调色板上只有两种颜色,或红绿,或蓝橙,或紫黄,《郑和下西洋》、《三星堆》用蓝橙,可调出正蓝、暖蓝、冷蓝,再由此不断演译暖或冷的灰蓝……《敦煌》、《丝绸之路》则用红与绿调制。2000年他和妻子露易斯合著出版了英文版的《绘画中的阴阳》,依据中国古老的阴阳互补的哲学原理,发现在绘画中用两种原色,可以推导出无尽的色彩变化。此书的出版,在美国影响极大,成为艺术畅销书。有读者反映说:“我的画再也不脏了”。
历史画中的张红年。他沉浸在自己的画作中,三千余年以来的历史,对于一般人来是多么遥远,多么陌生。而对他来说,似乎都是亲历者一样,在创作中不惜把自己也每每画进画里,参与政事。《酒池尽林》中他是被拖出去问斩的忠臣;《妇好征战》中右下角,一把尖刀,插入胸膛,那死不冥目的勇士;《焚书坑儒》中站在右上角记录这场惨案的史吏;《郑和下西洋》站在郑和身边的随员;《敦煌…》中的画师……。每幅画就象每出戏剧,都有他的角色,有他的位置,他是忠臣、勇士、史吏、画师。这不正说明他所追求的人生吗?
如今,张红年已六十开外的人了。电影梦虽未实现,但在历史画创作中他过足了导演瘾,享受着绘画中交响乐般的气势和力量。虽然,他现在是华裔美国人,但也是美藉华人,两种身份使他具有超越国界的眼光和胸怀,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立场上,在美国扮演着“中国文化使者”的角色,在世界艺术新潮流的涌动中,他仍不放弃对新艺术的追求,下次他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2008年5月10日 北京 名佳花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