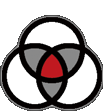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文化身份与个人身份 |
周彦
在与一些艺术家讨论时,经常会谈到当代艺术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艺术家如何在全球与地域的相关性中自处。换句话说,身处一个信息迅速传播、信息源走向个人化从而使得信息量急剧膨胀的世界,艺术家往往感到一种定位和方位的迷失,即是说,由于信息源与信息量的膨胀,人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变得不那么复杂和艰难,网络的语言愈来愈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适性或称世界性,我们会问,我们今天到底是一个“世界公民”,还是仍处于特定地域/地缘的个人?接下来的问题似乎应该是,有没有一种普泛的“世界文化身份”,或者艺术家的“文化身份”天然就是地域性/地缘性的?在一种“普世性文化”及其价值观与地域/地缘的文化和价值观冲突、互动、调谐的过程中,艺术家要如何“拔地而起”,即他应当如何建立和彰显他的“个人身份”?
文化身份和个人身份及其关系应当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历史上的元朝和清朝就给中原汉族的士大夫文人带来了极大的文化身份和个人身份的困扰。这种在异族文化甚至是“野蛮文化”占主导地位而使原有的汉族精英文化“屈居于下”的状况给“大汉”士大夫文人带来的“屈辱”和“挫折”我想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出世还是入世,为官还是为民,合作还是不合作,坚持理想还是屈从现实,在在都是困扰着知识分子的两难。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坚持自身的文化传承常常会和“复古”、“泥古”的困扰纠缠不清,而开拓新局又可能会与文化投降主义拉不开距离。元朝的“元四家”和清初的“四僧”便是艺术界挣扎于这种文化和艺术困扰之中的代表。具体而微,艺术家在他们的艺术中或抗争,或逃避,或冷嘲热讽,或犬儒调侃,或融古通今,独辟蹊径,都是在文化交锋的过程中或坚守自身文化或融合两种文化的手段,同时又因这种种手段的差异而形成了其艺术的“个人身份”。但是这里的文化融合与今天我们面对的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的大背景有一个根本的差别。这就是中原文化或称华夏文化在元和清时期仍属于主流的强势的文化,所谓“融合”是将一种“次文化”纳入主流文化的大结构中,主流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结构不变,在朝者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他们带入的“异族文化”面对的是有着千年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文化,这种文化强大到足以在政治上失势的时期仍然可以吸纳任何非华夏文化——在这里是所谓的“异族文化”——的成分而保持自身的“精粹”,融合是一个接受吸纳和充实的过程。
显然,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文化大环境,不仅华夏文化经过二十世纪的洗礼和蜕变,早已不是四百年前乃至八百年前的大汉中心的中原文化,世界文化的格局经过一两百年的洗牌已经把华夏文明从“中心”推到了“边缘”,文明古国的自豪乃至傲慢在新兴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强权的合力扫荡下几近荡然无存,传统的精英统治的文化日益世俗化,大众在政治话语权缺失的情形下,在商业和娱乐上的利益和趣味却被极大化了。传承五千年的文明却在二十世纪被边缘化产生的心有不甘或者无可奈何,眼见仅有两百年历史的强权以其强大军力财力和意识形态的强势摧枯拉朽,心生嫉羡又不得不佩服,成为今日的文化人普遍的心态。八十年代的现代艺术家曾经感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处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两座大山之间被挤压,发出“路在何方”的天问。这很有些像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着力研究的文化“游牧状态”(cultural diaspora,或译“背井离乡”)。一般而言,“游牧状态”的前提是跨地缘的迁徙,如犹太人的散居世界各地,英国罪犯的被放逐于澳洲大陆,从而产生的家园失落和文化的连根拔起。中国人的状态却迥然不同,尽管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大迁徙”的世纪,而且殖民者也在东部沿海建立了无数的称为“租界”的殖民飞地,但是民族国家始终存在,人口的主体也从未迁移到中华版图之外的地区。这种不伴随人口迁移的“游牧状态”,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自豪于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的世界最大民族经历着家园失落和文化失范的窘境,在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身份,真是叫人情何以堪!
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现代艺术家基本上面对的还是本土的问题,即延续五四时期的“传统与现代”、“革新与保守”的话题,论辩和争斗双方使用的要么是中国传统的精粹、要么是西方现代的理论和实践的武器。文化身份和个人身份的问题还只是在“传统还是现代”话题遮蔽下的隐性话题。到了九十年代,本土的文化和艺术的格局因着特定政治事件的发生产生了变化,而全球化的浪潮随着第二次经济改革和“入世”的步伐席卷了大陆,使中国的文化人和艺术家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洪流。八十年代反传统的前卫艺术家突然间面对一个更加凶猛的、更富张力的、更刺激的但更具挑战性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怪兽”,这是一个裹挟着西方资本和价值观的一些批评家称之为的“后殖民”的文化冲击波。可以说在面对这种新形势的九十年代,中国艺术家的应对还是非自觉的、被动的。九十年代初延续八十年代后期先锋艺术的“政治波普”和“新生代”艺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声,但是这些艺术家关注的仍然是本土问题,前者是对政治现状的曲折反应,后者则专注于“万马齐喑”下的个人生存状态和心理。前者有着如高名潞称之为的与主流意识形态处于“共犯结构”的硬伤,后者则难逃“文化逃避主义”的嫌疑,后来发展到“媚俗”也是其文化逻辑的“水到渠成”。真正在前卫艺术道路上蹒跚前行着的艺术家则退守于他们的公寓兼工作室潜心思考和制作要么是观念性的作品,要么是小规模或小尺寸的架上作品,没有公开展示的场所,很少媒体的曝光,更无商业的追捧。
讽刺的是,九十年代的“政治波普”和“新生代”即后来的“媚俗”艺术竟然不自觉地与世界性的“后殖民”处于一个更大的“共犯”结构中了。这里有当时国内的展示条件的限制的原因,使得大多数“政治波普”作品首先是在境外和海外亮相,而“媚俗”作品则率先在海外获得了商业的成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进入还是在九十年代后期的事情。由于这两类作品从商圈到博物馆,进而出现在严肃的重要的西方“双年展”中,因此在这种文化全球化的舞台上,它们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当代艺术中中国文化身份的代表。在这里,“个人身份”是消融在一种“大文化身份”中的,正如《时代》周刊刊登方力均的打哈欠的“光头”作品时,饶有趣味地称之为“解救中国的一声怒吼”,殊不知作者正在北京郊区的当时被许多圈中人视为“豪宅”的工作室兼住宅里享受着他的小资生活。这种被扭曲的“中国文化身份”却是九十年代国际政治和文化中的现实。造成这种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其一,九十年代的中国成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内部的政治现状和外部的冷战余绪合力塑造了一个后冷战时期的“冷战中国”形象,而这种形象背后深层的文化原因太复杂,无人费心也无需费心去深究。其二,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西方艺术处在一个“政治挂帅”的阶段,“身体艺术”中的身体成为政治抗议的战场,黑人罗德尼•金在洛杉矶被白人警察痛殴的录像被不加改动地搬进了纽约的惠特尼双年展,女性艺术和同性恋艺术则无不带有“民权”或“人权”的政治内涵。在这种大背景下,以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眼光观照当代中国艺术就成了某种“新观点”、“新角度”。其三,更为深层的艺术史和批评方面的成见使得这种意识形态性解读成为“自然”,因为在西方艺术史家和批评家眼里,当代中国艺术基本上没有一个美学的维度,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的艺术不是意识形态的附庸,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反叛,即是说它的“社会叙事”远远大于其“美学叙事”(高名潞语)。而且,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文化意味也被窄化为纯粹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这种简单化的解读常常令我们在海外的中国批评家为之气结。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什么是“当代的”并且“中国的”?在世界当代艺术史中,有没有名副其实的中国当代艺术?不管外人如何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一种战略性的思考,在世界艺术的格局中建造具有中国文化身份的当代艺术的一支?
我们常常会想,文化的传承是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的,无论艺术家做什么,怎么做,其作品的文化身份都是“天然的”。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没有文化的熏陶是一回事,是不是有意识地在思考中和作品中注入文化因素是另外一回事。八十年代文化身份是隐性问题,九十年代的文化身份则在全球化和后殖民浪潮中被不同程度地扭曲,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增强,文化身份的话题成了显性问题。在国内,批评家对“后殖民”日益敏感,本土出现的“文化游牧状态”即“身份不清”的状况逐渐引起关注,从反面说,一些强调中国身份的作品则被批评为“后殖民艺术”。在海外,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艺术家一方面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接受,另一方面则被国内批评家批评为操弄“中国符号”以迎合“后殖民”。而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是,随着互联网、游戏机、平面读物、电视和电影中的“卡通”长大的一代,生产出的大量“卡通艺术”,则极大地模糊了文化的边界,使其具有某种“世界文化”普遍性的特征,因而民族文化身份的问题似乎被消解在地球村的人们都能看懂且接受的“卡通”洪流中。更有甚之,在这个“去个性”、“去深度”、“平面化”的“后现代”艺术中,个人身份似乎也成了伪问题。
二零零五年,我曾呼应高名潞的“建立中国的艺术方法论和批评方法论”写过一篇“中国品牌和中国方法”的文章,借评论高名潞所作的《墙》展阐发我对“中国文化身份”的问题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或说先锋艺术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初创阶段,九十年代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边缘化阶段,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随着中国国力和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日增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尽管这种关注还多停留在商业性的拍卖场、新闻性的媒体上,但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逐渐展开教学和研究,学术性刊物上也开始出现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严肃讨论,而这正是作为八十年代充满理想主义的我们的理想之一,即所谓“与西方在现代艺术上作平等的对话”。但是,作为在海外讲授现代中国艺术史和当代中国艺术史的教师和研究者,我深觉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份之含混。这就是说,在讲授中国当代艺术史时,我们只有断代性的、按照时序的讲授一途,诸如八十年代的先锋派,九十年代的政治波普和“媚俗”艺术等,自然我们可以称之为“当代的”且“中国的”,但是我们没有一种可以和立体派、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之类匹敌的主义或者流派,或者像日本的“物派”那样的深具东方思想底蕴又风格独具的派别,一种有强烈文化身份、鲜明的现代性、但是又可以超越时空的艺术样式。
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八十年代反传统的先锋艺术家纷纷开始从本土传统中挖掘有益的资源。实际上,这种与传统的藕断丝连的关系在八十年代就没有中断过,尽管当时“全盘西化”是先锋派的旗帜。黄永砯、吴山专在其观念艺术中对于“禅宗”的活用(1985-1986),徐冰做“析世鉴”时直接使用活字印刷和古籍装帧的技术(1988),河北“米羊画室”的段秀苍、乔晓光和王焕青从民间和民俗传统中寻找灵感(1985-1986),在在都是利用和重新诠释传统的举措。即使在波普和行动艺术这种全然非传统的样式中,传统的因子也触目可见:王纪平的装置“旗”摆满了乡村酒肆的招幡;宋永红、宋永平兄弟的“一个场景的体验”中既有彩陶复制品作为道具,又有“做法”、“道场”般的仪式感。虽然没有形成系统地发掘传统资源的潮流,但是中国的现代艺术似乎从一开始就无法跳脱流淌在艺术家血液中的文化传承。九十年代的政治波普则已经把文革艺术作为传统来消费了,当然源头还可以回溯到吴山专八十年代用大字报方式做的“红色幽默系列:赤字”(1986)。而所谓的“中国极多主义”根据高名潞的研究是一种佛教禅宗的现代转化。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出国的一批艺术家那里,中国文化元素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是信手拈来,触目可见,例如徐冰的“英文书法”,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蔡国强的琳琅满目的火药作品,黄永砯的作品中出现多次的龙的形象和背后的中国哲学思想,陈箴体现了中国形式和当代问题的用马桶做的编钟,都在他们的艺术上打上了鲜明的中国烙印,因而彰显了它们的文化身份。
这种在艺术中使用中国元素的艺术在本世纪引起了一些争论,一些激烈的批评称之为以“中国符号”迎合西方的后殖民话语,仍然不脱所谓的“异国情调”,如同九十年代以“春卷艺术”所批评的那样,这类批评尤其指向那些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家。关于“中国符号”的争论是文化身份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当代艺术逐渐成为世界当代艺术中重要的一支时尤其如此。
文化的衍生其实是在地的风俗、习惯、人情、思维等的总和。传统上,这种文化总是与该文化中人出生和生活的地理和地缘环境直接相关的。直到殖民主义扩张出现后,文化的原初在地性即与生存地的直接地理地缘关系才开始有所松动,殖民者是最早的“游牧民族”之一(犹太人除外),他们来到被殖民的国家,文化的冲突、和解和融合即在新的“在地性”中展开。这种关系在九十年代至本世纪的海外中国艺术家那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谷文达、黄永砯是八十年代已在国内展露头角的艺术家,如果说他们八十年代的文化身份还被他们的反传统观念的艺术所遮蔽的话,离开中国到法国和美国倒为他们提供了凸现自己文化身份的环境。这种文化身份的突显既有主观的故意,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客观的环境变化使他们做出的调整。因此浙江或厦门的“在地性” 转换成了纽约或巴黎的“在地性”,谷文达就谈到过他在美国遇到的“在地”的文化冲突,这里面有“东方”与“女权”的冲突(如在他的月经带作品计划中与博物馆的冲突),有处于东方与西方夹缝中的尴尬(如他在瑞典的《国际刑警》展中的头发装置被俄国艺术家摧毁的事件)。这里的文化身份的出现有的是被动的或处于防御性的态势使然,换句话说,你的文化身份不是你故意的张扬,而是被“自然地”做的连接。而在另外的情境下,艺术家则是主动地以自身文化的资源作依托,重新加以诠释,与不同文化对话,如徐冰的“英文书法”,谷文达的“碑林”,蔡国强的“草船借箭”,等。
在这些艺术家那里,文化身份的体现有时是以符号和元素的形式出现,如“英文书法”和“碑林”,有的是以观念和战略的贯穿显出,如“草船借箭”。黄永砯的“蝙蝠计划”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身份的最恰当的艺术诠释之一。它的复杂性体现在作为法国公民的黄永砯是华裔的艺术家,而他的作品所指涉的却是美国与中国的一次重大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冲突,而美国领事馆对作品参展的干预又是通过法国领事馆间接实现,这里面夹杂的多文化、多民族的情结的交错和缠绕,凸现了当今世界上文化冲突的激烈和复杂,也许单一的界限清晰的文化身份已变得越来越模糊,因而越来越不可能。而且“在地性”和“全球性”在这个个案中也纠缠在一起,很难说它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和作品,可是它又是确确实实发生在中国南海和深圳的事件,而且黄永砯的“蝙蝠计划”终究还是局限于艺术界的“地方性”中的事件。但是不管怎么说,黄永砯的“蝙蝠计划”中的飞机如今还是在深圳OCT艺术中心外展示,这半架美国间谍飞机的复制品的“中国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在全球化中的文化身份的复杂和纠缠在住在北京的东北艺术家沈少民的观察和作品中有着非常奇特的状况和特殊的意义,即在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边境地区出现的人种混杂、文化混杂的情形。在青年批评家杜曦云的一篇访谈中,沈少民说到,
在黑龙江两岸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中国。在中国这边很偏僻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目前还有75%是混血儿,东北冬天酷寒之下有半年冰封江面,因为这里江面比较窄,随便就可以溜过去,以前的边境封锁的也不是很严,所以两岸之间有一百多年的通婚历史。加上历史原因,一战、二战还有十月革命,有很多白俄被打过来,二战时很多男人都战死,留下的好多寡妇带着孩子,她们都跑到中国这边嫁给中国的农民,移民,就这样繁衍下去了。在中苏交恶期间,珍宝岛打仗,中苏边境封锁较严,这种通婚就断绝了。再加上地理原因,这里非常偏僻,就逐渐变成了近亲结婚,人种就变异了。在通常印象中混血应该长得很漂亮,但那里人的相貌就很奇怪。那里的人酗酒,加之东北的地理环境,一年有六个月什么都不能干,冰天雪地无事可做,所以每天赌博、酗酒。还有两个月是农闲,就是说一年有八个月的时间没有事做,加上酗酒的习惯,非常无聊。有的人中国话说不清楚,俄语也说不清楚,也没有国籍,文化身份都不清楚,文革的时候,因为这些原因,被定性为苏修特务,其实这些与他们毫无关系。所以,政治重压之下,有自杀的、跳井的。他们是杂交的,从文化到人种。包括宗教信仰,他们有信佛的,也有信仰基督的。文化上的差异很大,饮食习惯差异也大,他们的生活习惯,保持着俄罗斯传统,老人还保留着烤面包炉等……他们都是一口东北口音,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但是脸又是欧洲人的特征。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极端的文化身份混淆的案例,它首先源于人种的杂交,政治和社会的因素介入,宗教的混杂,最后在语言、习俗、甚至个性上产生了裂变和混淆,忠实地记录这种现实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作品,一定有十分震撼的效果。
这种极端的情形在艺术中虽然不多见,但是今天的情境比1980年代要复杂得多则是毋庸置疑的。二十世纪初,因着西学和西艺的引进,“国画”的概念产生以因应艺术中文化身份的模糊乃至丢失的危机,五十年代中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通过一批中国学生在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的学习和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传授而引入,不久后便有所谓“油画民族化”的口号出现,剔除这个口号的意识形态因素,这个口号凸现的也是一个有别于“苏联油画”的艺术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八十年代先锋艺术家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多种文化的复合体,其中有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延安继承而来的革命艺术后来演变成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文革中更极端化为一种意识形态至上的宣传性艺术,文人艺术和民间艺术以及徐悲鸿等引进的法国十九世纪学院艺术,这种多文化的复合体成为一种新传统而成为先锋派反对的对象,而此时文化身份的话题被“现代化”的话题所遮蔽,因为当务之急是观念更新和话语革命。九十年代的政治波普和媚俗艺术在海外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呈现着当代中国文化的身份,在国内则因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以及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影响,出现了卡通化的身份模糊的艺术。而在这期间,有一批在商业和体制上都处于边缘状态的艺术家在一直继续着八十年代的精神之旅,虽然观念上并不十分清晰,但骨子里一直是在想着做一种既是东方的又是当代的艺术,他们和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出国的一批艺术家都同样面对各自的“在地”问题。如果说后者的“在地”问题主要是在与不同的文化的冲突中凸现,前者的“在地”问题则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内心的冲突,而所谓的边缘化反倒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沉静的个人的思想空间。以一种开放的心态读陆游的“咏梅”,可以说是这批艺术家的心灵写照,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是商业艺术和官方艺术之外的“第三空间”艺术,是仍然保持着某种出世心态的精英艺术,其中也有卖得不错的,或是身为体制中人的,但是要紧的是那种清流心态和东方智慧的结合,身处红尘却依然拥有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笃定。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了高名潞寄来的新展览的文章草稿。他最近策划的在北京和西班牙展出的《意派:中国抽象三十年》展览是多年来苦苦追寻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和个人身份相结合的流派所做的努力的结果。在读了他的相同标题的图录文章的草稿后,我发了这样一番感慨,
中国“抽象”三十年,也是我们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三十年,现在终于有了集大成的“意派”的总结,有种理想实现的感觉!当年的奋斗如今终于结出了果实。当然是你这么多年来策展、写作尤其是苦苦求索的结果,艺术百姓创造历史,你则是写历史,同时也创造历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意派”在世界上立起来,理直气壮地纳入世界现代艺术史,终于到了中国艺术向世界现代艺术作出实质性贡献的时候了!
从他的总结性概括和分析中,我看到了一代人的努力如今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初结出了沉甸甸的精神果实。关于“意派”的具体讨论,我不想在此多费口舌,高名潞的展览和文章有非常翔实的材料供我们了解和研究。我只是简单地提取他关于“意派”的界定,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按照他的界定,“意派”就是主张把“明志”(鲜明的人生态度以及独立的行为方式)和“立象以尽意”(视觉和观念不极端分离的视觉形式)两者融为一体的中国当代艺术。它的精神和形式的特征被概括为,
这种似乎带有“极少主义”外观的中国“意派”艺术表达了艺术家对新的都市流行文化的疏离和自我放逐、自甘边缘的情绪。所有这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和构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那些方块、点和线既不是纯粹的物质性的装饰,也不是极端精神性的乌托邦理念,而是类似日常生活中人与物的对话过程。它是日常生活中的重复琐碎感觉的再现。是都市化生活中的自我疏离于外界的精神寄托。这种“意派”形式不是重在对绘画形式的物质性的再现。因此,它的“极少主义”的外观与美国1950年代的“极少主义”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是类似冥想和参禅之类的精神活动的纪录。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这类的“意派”艺术家都强调重复性、连续性和朴素不造作的心态。因此注重修心自足的精神无限性。
在艺术作品的空间形式方面,中国的“意派”艺术, (比如“极多主义”Maximalism)追求空间的“无限性”(infinity)。中国的“极多主义”艺术家们对有主次对比和有中心边缘之分的“整体性”(wholeness) 构图形式一般不感兴趣。他们一般不试图创造一张或者数张独立完整的“画”。相反,他们追求在多个系列作品中表达自己的空间观念。所以,他们的作品大多是由重复的系列组成。所谓“完整”的概念是在诸多个不完整的个体中实现的。所以,在中国的“意派”艺术家看来,不存在着一个固定的、被一个画框所限定的孤立、静止的空间。空间是一种关系,它总是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
高名潞一再强调不是他在创造历史,而是艺术家在这三十年来创造了作品,形成了历史,而他只不过是梳理出了这一条线索。我觉得,这种梳理正是今天我们的批评家和当代艺术史家所迫切需要做的工作,这里体现出了一种战略性的眼光,那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在走过三十年筚路蓝缕的历程之后,我们不能再象狗熊掰玉米那样,一路掰,却又一路丢,而应当从中整理出历史的积淀,文化的积淀,艺术的积淀,从而在一种坚实的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上,总结出具有艺术史意义的流派、艺术家和美学。“意派”的总结是独特的、真实的,可以放在艺术史中供人讨论、批评却不可能绕开的,虽然它可能不是唯一的。要点在于它是中国的,当代的。我觉得,“中国的”体现在其中隐约见出的文人精神和情操,以及文人艺术的美学观念;而“当代的”则体现在它传达的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全球化、都市化和消费主义大潮中的心境和心态,而在形式上又融合借鉴了许多二十世纪艺术的元素,而那在文人艺术中几乎是见不到的。
至于“意派”的精神价值,高名潞这样说,
似乎可以说,“意派”是中国当代的文人艺术。它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疏离性和在媚俗时尚中保持自我完善的人性品格。这种自我完善恰恰是当前中国所缺少的个性基本素质,也就是一个民主社会所必须建树的人格品质。
因此,文化身份的话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中国精神的话题,因为它不同于种族身份、职业身份、或者性别身份,没有外貌的、专业的或身体的直接特征加以鉴别。它是通过外部的形式特征传达出一种有别于其它文化的精神特征,这里面包含历史的、文明的、哲学的和道德的种种因子,而且又和当下的中国现实以及海外中国人的“在地”现实密切相关。而由于每个人对历史、文明、哲学和道德的了解、理解深度和广度的差别,以及对当下现实的体会和观察的角度与切入点的区别,艺术家的个人身份于是得以彰显。个人身份虽然和我们常说的个性相关,但不等于个性,它不是个人性格、情趣、喜好的“自然流露”,而是独立的个人长期钻研、观察、思考的“刻意为之”;它不是表现主义性的情绪宣泄,而是深思熟虑的智慧的结晶;它需要的常常不是即兴的、信手拈来的灵感火花,而是长期阅读历史和人生的水到渠成。这种个人身份的突显,常常是与时俱进的,即它是对周遭的变化着的现实的应对;但它又是恒定的,那就是一种精神的坚持与执著,并不因时世的变化而改变,体现在艺术形式上则应能见出一种逻辑或连续性,即既有历史的文脉又有个人的发展逻辑。在今天这个“图像社会”,人们大多数的信息来源都是从电视、网络、平面媒体的图像中摄取,这种无需太多大脑筛选、过滤的信息只能提供表层的平面的瞬间印象,甚至有“去智化”、“失语化”的危险。对于今天的艺术家而言,用文字吸收信息,以文字进行脑力激荡和思考,成了一种“奢侈”,因而也就成了一种当务之急,很难想象没有真正读过几本哲学、历史、美术史的艺术家会去思考并且能够真正领会所谓文化身份和个人身份的问题,从而创造出真正中国的、当代的艺术来。
文化身份和个人身份的话题是一个宏观的、战略性的话题,需要我们的批评家、教育家、策展人、艺术史家的协同努力;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微观的、战术性的课题,是需要每一个艺术家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非常个人化的劳作。崛起的中国需要坚实的文化身份的衬托,而文化身份的确立和彰显又是在崛起中获得助力的。屹立于现代世界的文化中国曾经是一个古老的梦,古老的神话,如今,梦想已有成真的机遇和大环境,在此,当代艺术家不能缺席。
二零零八年三月
(本文为2008年中国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实验艺术教学》研讨会论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