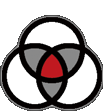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我们能走出“文化低谷”吗? |
周彦
一九八七年,曾有朋友预测未来十年的中国,将是一个文化低潮时期(当然这里主要指一般所谓“无形文化”或曰“精神文化”),理由至少有二:一代领导人的工作重点是全力以赴抓经济改革;其次,芸芸众生亦随着经济大潮的裹挟而逐利于市场。上下两方面少有或根本没肴闲暇来关注这些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事业”。对此,我曾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总有一批孜孜于文化事业的人,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始终在奋斗着,“沙漠化”的危机似乎不可能出现。但今年以来,愈来愈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文化低谷已经比我们预料的来得更快。
“0”状态
我不知从农业文明走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是否有过这种文化低谷的时期,在华夏大地上,这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先不说如今“君子言利不言义”的现状,也不说学术、文化正在以比货币更快的速度贬值,这些只能说是文化低谷的表征,更深一层的低谷是在精神上,我称之为“0”状态。精神上的这种“0”状态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去看。
“一无所有”——青年的普遍心态 恐怕从来没有一首歌曲能像崔健的“一无所有”那样能如此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一代青年的普遍心态,这首看似爱情歌曲的“中国摇滚”实际上是以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有悲怆、失望、伤感而又不甘沉沦等——唱出了一种社会心理,或者说唱出了“文化”。笔者曾去首都体育馆看过一次由崔健压轴的摇滚音乐会,令我震惊的既不是体育馆门口那万头攒动的青年人自己过节的气氛,也不是场内那震耳欲聋的架子鼓、电吉他和着那嘶哑的“吼唱”组成的“Chinese Rock",而是全场几万人自动和着崔健齐唱“一无所有”的情形,我被这种完全发自内心的呼号深深地震撼了。类似的情形只是在“文革”中开大会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见到过,但两者的根本区别是:后者服从外在的统一指挥,前者则完全是自发的、发自心底的。参加音乐会的无疑绝大多数是青年,并且不少是大学生、研究生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据说北大还成立了“崔健后援会”)。青年的状况、尤其是青年的心态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晴雨计”,在现代文明中尤其如此,美国文化就是这种“青年型文化”的一种最好代表。“一无所有”不仅仅是指物质、金钱的匮乏,更主要的是地位的低下、参与权的被剥夺、生命活力的被钳制,以及由此导致的迷茫、失落、压抑、怅惘、困惑与幻灭感,国门开放后的“世纪病”——荒诞意帜在一些较高层次的青年人中产生了,它的哲学意蕴就是:存在的无意义,人生的无意义。在我看来,哪一种危机都没有这种危机来得更带有根本性,这种“空”与“无”的精神状态本身并无消极、积极可言,其效应完全在于其导向(容后述)。但它无疑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值得密切关注的新的文化态势。古语曰,“哀莫大于心死”,这种自觉“一无所有”的心态是文化低谷时期的最为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
从“自我感觉良好”到自觉“什么都不是”的文化人 一九八七年各方面形势的急剧发展,冲击了一大批曾经“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化人,尤其是其中的青年学者、文艺家们。前些年,文、史、哲等诸领域异常括跃,文化人们的自信心空前高涨,但好景不长。一九八七年以来,各种报刊、杂志上难得见到值得反复咀嚼的力作,美术馆、音乐厅要么是西方古典、要么是矫饰扭捏的国人作品登场,总是刺激不起人们的情绪趋于亢奋。有一位国内著名学者的弟子、社会科学最高研究学府的研究生曾发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慨叹:爬格子吧,实在难以果腹;做生意吧,不光两手空空,更无钻营之道;出国去吧,打字、电脑操作一概不会,只能去干苦不堪言的下活,生存危机这柄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我们现在才发现,受了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教育的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竟显得如此的无能!不要说那通篇宏论、艺术大作在经商大潮中声音微乎其微,于经邦济世并无多大效用,甚至自己的生存都产生了危机,举步维艰竞至于此!文化人的“什么都不是”的这种自我感觉,自信心的一落千丈,起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从外部看,是教育的失败,是畸形文明结出的苦果,更重要的是自身与社会之间从根本上缺乏一种“榫卯关系”,社会需求与自身条件之间完全相左。此外,国门刚开时,主要是引进、介绍先进文化的成果,繁荣背后确有贫血的背景,在这个能将任何先进的东西都加以“变形”、“歪曲”的文化面前,找到一种既是现代的、又是在本土上行之有效的良方确实需要时间,这个任务无情地选择着执行者,短时间内恐怕很难有一批合格的精通域外先进文化、又深谙本土文化底蕴的人选出现,低谷时期势不可免。
缺乏领袖的时代 文化的兴盛,与各个领域有少数众望所归的领袖性人物关系极大。我这里指的主要是精神性的领袖。显而易见,我们面临的正是一个缺乏精神领袖的时代,所谓“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还不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势态,这种“英雄”也还不是现代意义的领袖。这是因为,真正能够在当下各种利益集团、各个领域中统领全局的人的出现,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运动的结果,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思潮发展的“水到渠成”,真正的凝聚力产生于一种最高的精神追求。这就如同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的真正领袖既不是罗伯斯庇尔,也不是拿破仑,而是孟德斯鸿、伏尔泰和卢梭等这样一批启蒙思想家一样,“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三权分立”这些近代文明的精神大du(上为“毒”,下为“县”之繁体)正是他们打出来,而唤醒千百万人为之浴血奋斗的。故而,缺乏领袖,实际上是缺乏思想家,因此,知识大众、一代青年的精神、思想,使不能不出现令人惊俱的空白,纯粹西方的、纯粹中国古典的哲学、政治、经济、文艺等的思想都不能在当下的文化中直接生效,这个最要命的空白是文化低谷时期出现的根本原因。
走出低谷的几条思路
上面描绘的似乎是一幅黯淡的社会心态图,但是,正如不能对前些年的文化繁荣气象盲目乐观一样,我们也不应对眼下的精神“0”状态抱绝对的悲观情绪,“直面惨淡人生”是一回事,分析形势、寻找对策则是更重要的任务。首先要肯定的是,走出文化低谷、重建中国文化是一代人的使命,何时使我们的“老年文化”向“青年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折,那便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曙光。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否可以从以下几条思路来思考:
将精神危机推倒荒诞极致 从一种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所谓的精神的“0”状态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无”状态,而毋宁说它是一种进步。何以见得?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说的从神性走向人性、从神权走向人权、从神道走向人道的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决不是一个美好得没有瑕疵的阶段,相反,从另一种角度看,那是一个人欲横流、利欲熏心的时代,神圣的跌落以后,最为亢奋的决非真、善、美的美好追求,而是久被压抑的人性的最基本需求以失控的集体无意识形态产生的大爆发,《十日谈》恐怕只不过是这个阶段的一种较为纯洁的写照罢了。但是,文明并未因此衰落,近代文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来,关键还是对集体无意识的导向。我们眼下的情境与之相似之处在于,原有的精神支柱坍塌了,禁欲主义、重义轻利、扬文抑商、官本位意识等一系列的规范、准则正在被打破,“变了形”的舶来品又不能真正填补“精神真空”,故呈现出精神“0”状态。但这有如一根座标横轴上的“0”点,我们从“负”回“0”,有何“倒退”之虞?“0”是“负”的终极,但它更是“正”的起点。问题是,我们是否已彻底回“0”?换言之,我们在发展曲线上是否完全走入了谷底?回答应当是“还没有”。文化的最要命的状态恐怕就是那种半死不活的温吞水状态,“置之死地而后
生”似乎从未在我们的文化中出现过。在当下,由“一无所有”的心态向彻底的荒诞意识——存在、人生的无意义——的发展并没有在大多数青年那里完成,发些小财还有门道,出国淘金也似乎满有希望,人生的意义还大多维系在一种可怜的眼前功利上,这仍是半死不活的苍白状态,没有大彻大悟的境界,恐怕永远也跌不到谷底,因而永远也走不出低谷。故而,只有将精神危机推到荒诞极致,即不仅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尤其是广大青年都发现他们终日孜孜以求的东西竟是毫无意义的,虽然发了一些小财、或爬上一个比以往高一点的地位,但人的尊严、生命的本真状态都失却了时,才会想一想“人活着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才会发现付出的一切却造就了一个外在于自我、束缚或剥夺自我的异我,才会悟出“人即是人自身的悖论”这样的真谛。有一位从澳洲回来办移民手续的画家朋友对我说,你只有从人家的白眼中才痛苦地感到自己永远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中国人!国人的这种精神困境恐怕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这种心态正常发展下去只有走入彻底的荒诞!傻呵呵地继续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只能使我们总是处于苟且偷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可怜境地!走入哲学意义的彻底荒诞有如精神的“凤凰涅槃”,非如此不能真正思考人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存在的本质这种最高的精神性问题,非如此不能使人们从内心生发出重建精神上帝的渴求,自然,精神领袖、思想家也就不可能出现,因为这种领袖不是外加的,而是众望所归的。这种近乎悖论的思路恐怕不失为一种值得一试的路径。我从北京工人体育馆门口经过时,看到一幅大广告牌上赫然写着“救心”二字(那只是一种心脏病急救药的广告),使得我大大地震撼了!“民主救国”也好,“科学救国”也好,“教育救国”也好,都还只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提出的策略,从价值理性的角度、从存在论哲学的高度出发,“救国”莫如“救心”!而要“救心”,必从毁灭中获得再生,在烈火中使凤凰得以“涅槃”!
争取成为各种新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现在的经济格局、利益关系虽:然让人扑朔迷离,呈现一种无序状态,但它是从原来僵硬的有序向新的趋于合理的有序过渡的阶段。我们当然不能一下子就勾划出一种新格局,但是,可以想见,通过分化、瓦解,进而重新组合,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要出现各种新的利益集团,多元的精神文化应当说正是建立在多元的利益集团基础之上的。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文化考虑,我们应当研究这些可能出现的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将要提出的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等方面的新要求,或许我们自身也
将成为某个利益集团中与之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一分子,具有现代的哲学头脑、政治思想、经济管理才干、法律知识、艺术创造能力的文化人便既是责无旁贷、也应当仁不让地成为各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囿于各自的近期利益、任务,这些集团的领导者、操作者们不可能有太多精力和能力去在更大的范围考虑战略性的全局问题,考虑长远的整体策划,故而代言人的作用就十分的重要了。实际上,新的精神文化并不是产生于真空,而正是从这种基础性的文化背景中生发出来的,既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既讲求功利又能超脱一己私利的精英分子当是新的精神文化的执牛耳者。(精英知识分子阶层自身亦应形成有力的具有文化导向性的利益集团,这里恕不详论。)
建立文化市场 时势已使得纯学术、纯艺术的研究、创造愈来愈困难,既然任何学术、艺术都应与人相关,与人的生存、环境、发展相关,我们就应从这个前提出发,研究文化与当下的经济变革大环境的关系。在一时出不了重大的文化成果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变革之风,培育我们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文化市场,在市场与精神文化间建立起良性的循环。别的领域不说,单就笔者熟悉的美术领域而言,已有一些人在认真研究西方的画廊制度、经纪人制度及画商体系的情况,可以不夸张地说,西方现代艺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批评家与画商“制造”出来的文化“怪物”。市场经济中的职业画家,艺术品的出卖与购藏及其相应的一系列价格体系、经纪人、画商、画廊、拍卖行等,应当成为建立我们的艺术市场体系的大目标,其它领域亦当如此。自然,这有赖于经济的长足进展,有赖于一批具有文化眼光的经济实体及其实业家的出现,因此这个问题又是与前述“代言人”问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市场小环境的建立,将是精神文化走出低谷、重振雄风的良好征兆。
当然,文化低谷既是文化诸要素的合力造成的,最终仍须由诸要素共同来促使其走出低谷,时间可能不止十年,也可能走不出去,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
一九八八年九月于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读书》杂志(月刊)1988年第12期5-9页)
(附:该期《读书》杂志“编后絮语”摘录:
由知识分子问题自然会考虑到中国文化问题。现在中国的“文化热”已经变成“文化冷”。照本期周彦的说法,中国正处于“文化低谷”之中。既云“低谷”,必有高峰,我们大可不必悲观。但是,如何走出低谷,实在是一件费斟酌的事。我们希望就周彦的想法提出一些话头,以后有更长足的讨论。 ——160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