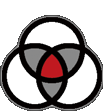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中国品牌和中国方法 |
受段君启发也评高名潞的《墙》展
周 彦
在“美术同盟”网上看到段君“向前的逃跑:评高名潞的《墙》展”一文,有些感触。把一个严肃的展览看成门户的争斗,在我看来格局似乎小了点。一个展览开幕,众说纷纭本来很正常,对策划者的选题,选艺术家,直到布展的构思等等意见不一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批评要让人信服,批评者应该认真地看过展览,仔细地读过图录的文章,真正理解了策划者的意图,去除情感化的反应,然后下笔著文,才能客观的评论一个如此大型的展览。我正好也在美国看了这个展览,于是也来评论一番。
高名潞策划的《墙:中国当代艺术主题展》展览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展出一个月后,从北京移师美国,十月二十日开始在纽约州水牛城的三处展出,分别是纽约州立水牛城大学北校区的艺术中心,该校南校区的安德逊画廊,以及该市著名的阿尔布赖特—诺克斯美术馆。展期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长达三月余。有如此难得的中国当代艺术大展,笔者专程驱车近六小时赶至水牛城,颇有“千里迢迢,恭迎盛会”的感觉。
尽管事前已有一册展览图录在手,现场观看作品和栖身行为艺术现场还是让我觉得不虚此行。开幕的主题发言和高名潞的论辩尤其使得展览一开始就充满张力。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1990)一书作者,开幕式的主题发言者阿瑟•瓦德戎 (Arthur Waldron) 以权威的口吻评说长城的历史。基于文献的考证,瓦德戎教授考察了长城的历史,认为二十世纪长城成了中国民族的象征,1949年后更成了官方推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符号。他的发言口气流露出对作为符号象征的长城的不屑和轻蔑。这个主题发言结束后高名潞站起来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考察长城不能仅仅从文献入手,长城首先是个建筑物,一个实体,它的象征意义,文化意义的演变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现实和文化脉络密切相关的。比如,长城确立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并且物化为一座民族的纪念碑是在八年抗日战争其间(高名潞在图录的“重构历史记忆:20世纪中国艺术中的长城”一章做了详细讨论)。关于这一点,作为历史学者的瓦德戎教授并没有注意到。长城对于中国人和艺术家来说远比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符号要复杂和深刻得多。根据笔者的观察,美国学界对中国的研究还是“意识形态批评”的路子为主。这一方面基于中国的制度政情,一方面还是冷战意识形态的遗留。而且,意识形态的非黑即白的批评其实也是一种最省事的方法,可是运用到实际研究中不是显得肤浅片面就是充满偏见。虽然慢慢地也有学者试图从中国文化的上下文和当代现实的互动出发,试图走“去意识形态化”的路子,可是基本上这种路子还远未被大多数学者采纳。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学术性误读” 还是大量存在。尤其在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文化主流的今日,“意识形态至上”似乎也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标签。从这一个小时的开幕式出来后,高名潞很高兴,因为有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和一个美国的保守主义学者正面交锋,也是对一种“学术性傲慢”的直接抵制。
四川艺术家陈秋林接下来在宽敞的艺术中心大厅重做了她2003年“我存在,我消费,我快乐”的行为艺术:八个壮汉(估计都是学校的本科学生)向八个方向拉一辆商场的购物车,艺术家本人则身着白色婚纱坐在购物车里化妆。当其中一人在这种“拔河比赛”中取胜即够到了他前面的一盘蛋糕后,他便成了“新郎”,于是抱起“新娘”,与“新娘”合影。对于这个娱乐性很强的行为艺术,观者最后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是为艺术鼓掌还是为那个得胜的小伙子“抱得美人归”鼓掌?也许两者都有。在我看来,这个集中国古代“抢亲”仪式和今日消费方式于一体的行为,是艺术家一个很巧妙的创作:在完全娱乐的气氛中用“快乐而美丽的鞭子”抽打了中国当代消费主义的现实,女性成为消费中心的同时也被人消费着,传统与当代的“联姻”正是当下中国“现代性解决”的实施。可是这件作品搬到美国这个消费主义的“老巢”似乎又有了另一层意义:“公平”的市场规则其实是力量的较量,西方要分食中国市场这个当今的世界“魅力中心”的大饼端看谁拥有超级的市场力量了,传统的“实力至上”的丛林规则似乎有着恒常的生命力。
和一九八九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一个相似之处是,行为艺术再一次抢得了媒体的关注点。生于云南现居北京的艺术家何云昌于展览开幕的第二天在阿尔布赖特—诺克斯美术馆前把自己的身体陷入到灌满混凝土的大容器中就已经让观众瞠目结舌。表演在美术馆的室外广场举行。何云昌赤身坐在一个特制的比他还高的透明容器中,一个水泥浇灌车直接向容器内浇灌水泥直到淹没他的胸口。当晚天气极冷,何云昌冷得浑身发抖,并忍受着水泥的凝固压力。美国观众对这种拼命三郎的“中国人精神”极为钦佩。有的观众在看到何云昌的痛苦时,高喊着要立即将他从容器中救出,但被何云昌坚定地拒绝。直到一个小时后水泥完全凝固, 工人们敲开水泥将他从“水泥柱”里扒出来时,他的全身皮肤由于水泥的侵蚀已经破裂。但是,第二天一早,何云昌就又赶到尼亚加拉大瀑布进行了一次“未遂”的行为艺术。他原计划站到水流下落的悬崖上二十四小时。但是,在他刚进入水中时,立即被游客发现并报警,他离瀑布的悬崖边只差十几米。警察将他带走,并留在医院二十四小时(多么不同的“二十四小时”!),检查精神和心理是否失常。消息立即被美联社详细报道并被很多家媒体转载,以至成为了一个“世界性新闻”。要点不是他在接近零度气温下赤身步入河中,而是随后的被捕,理由是“行为不当”。与自然抗衡的作品最后成了与制度抗衡的结局。和肖鲁唐宋被关了三天未经审判被释放不同的是,何云昌的案子上了法庭。布法罗大学和阿尔布赖特—诺克斯美术馆方面为他延聘了律师。律师的辩护自然是从艺术的角度解释他的行为,而法官也基本同意“撤销”这个案子。但是尼亚加拉市政当局和警察局方面还有异议,不过艺术家本人已经释放,大难不死的他去纽约“考察”艺术去了。十一月四日,法院以“如果在六个月中不发生违法行为,将撤销此案”作为结束,何云昌本人则被罚200美金。 高名潞在布法罗大学的两个美国学生由于帮助何云昌(开车、摄影、录像等)每人也被罚款200美金,理由是“参与不当行为”。但是,何云昌对这些新闻事件似乎并不感兴趣,他对没有最终实现它的计划仍然深感遗憾。他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从没有实现过的壮丽景观,一个人站在大瀑布悬崖边的水中二十四小时,体验着生命和大自然的抗衡。
不过何云昌的“锋头”并没有掩盖展览中其它作品,接下来三个多月的展览仍然平静地向观众展示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成果,在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的节假日期间,相信可以吸引较多的观众。同时阿尔布赖特—诺克斯美术馆还会在这三个月中逐一放映参展的当代电影,依序是欧宁和曹斐的“三元里”,杨福东的“陌生天堂”,章明的“巫山云雨”,贾樟柯的“小武”,和王兵的“铁西区”(共三集,分三次放映)。
进入展馆,我脑子里浮现出“中国品牌”这四个字。如果说1998年在纽约展出的“Inside Out: New Chinese Art”(我试着把它译成“从里到外:中国新艺术”)展览是高名潞在历史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大陆和港台现代艺术的较全面的展示,2005年的《墙:中国当代艺术主题展》(英文标题 “The Wall: Reshaping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则可以看成他试图推出“中国品牌”的当代艺术的进一步尝试。前一个展览包含1980年代高名潞界定为“理性之潮”,“生命之流”和“后’85”反艺术的作品,1990年代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公寓艺术”“观念艺术”等,以及台湾和香港的当代艺术。这些艺术样式不能说不是一种“中国品牌”,不过在全球化以及后殖民主义的当代艺术的大背景下,其“地方性”大于“全球性”,支撑此品牌的理论基石仍显薄弱,或者说推出品牌并非此展的主旨。之后,高名潞明显地着力于品牌的建设,《中国极多主义》展(2003)就是一次重要的试验。和极少主义讲究“剧场效果”的形式而排斥意义和精神的取向相反,“极多主义”以“无意义”的形式记录精神的流程。与十八位艺术家的作品相辅相成,高名潞在此展图录中发表了他洋洋二万言的“中国‘极多主义’:一种另类‘形而上’艺术”一文,讨论了中国“极多主义”的定义和发生背景,“极多主义”的方法论,并认为这是一种可以共享的方法论。这里的方法论被高名潞分析为“反表现,反再现”;“形而上运作”;“意义只存在于过程之中”;“定量与无限”;和“归宿:禅?” 这里包含宗旨,操作方式,意义的生成,能指的界定和发展的指向,足以构成一种方法论的框架。为中国当代艺术之一支作一种方法论构建,这本身就是一种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
如果说艺术方法论的构建乃是一种起步性的奠基工作,艺术批评和历史方法论的建设则是更根本的带有战略性的工程。当我们不满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化”批评,又不能满足于中国传统的经验主义批评时,无疑应当下功夫研究和努力建设能有效地准确地对当代中国艺术史进行分析批评的方法论,非如此无法理清二十多年来当代艺术错综复杂的发展线索,或者只能简单地以“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形式与内容”,“政治与艺术”,“官方与地下(或“反官方”)”,“集体与个人”,“自然与文化”,“社会与美学”,“能指与所指”,“视觉与文本”,“共性与个性”和“公共的与私人的”等这样一些二元对立的“现成品”词语来框定和解说。也有的批评家和史家借用某一个或几个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当代艺术,却往往由于时空的差异要么像隔靴搔痒,要么显得牵强武断。有感于多年来如同“狗熊掰棒子”似的批评发展,高名潞深感已经到了清理二十年的批评实践,建设中国艺术批评和历史方法论的时候了。
方法论的建设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西方的现代艺术批评和历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复杂而庞大的体系。今年刚出版的杰•艾莫凌(Jae Emerling,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新书《艺术史理论》(Theory for Art History)一书,把弗洛伊德,马克思,尼采,索緖尔视为艺术史理论的先驱,接下来讨论了二十二位二十世纪重要的对艺术史理论影响至巨至深的人物,包括阿多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阿尔道塞,巴蒂欧(Alain Badiou),罗兰•巴特,巴泰里(Georges Bataille),波德瑞那尔(Jean Baudrillard),本雅明,波尔狄欧(Pierre Bourdieu),巴特勒(Judith Butler),德鲁兹和瓜塔瑞(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德里达,福科,海德格尔,伊里伽瑞(Luce Irigaray),克里斯特娃(Julie Kristeva),拉康,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利奥塔德,梅罗-庞蒂,萨伊德,和斯派瓦克 (Gayatri C. Spivak)。从这个长长的但不一定完整的名单中(注意:这里不包括艺术史家,所以做图像学研究的潘诺夫斯基不在其中,沃尔夫林,里格尔,瓦柏格和冈布里奇也不在其中),我们大体上可以缕出一条从精神分析,社会分析,结构主义,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语义学,后结构主义,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 阿甘本为代表),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巴特勒,伊里伽瑞和克里斯特娃为代表)和后殖民主义(萨伊德和斯派瓦克为代表)这样一条大线索(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单里除了一两个美国人之外,基本上是欧洲大陆的思想家或美术史论学者,所以连“欧美中心”都谈不上,只能说是很地道的“欧洲中心”,而且是美国学者认可的“欧洲中心”)。这里的人物有一半左右是哲学家,其他的无不具有深厚的哲学修养,这说明理论的建树首先需要的是哲人的智慧,修养,洞见和逻辑。中国传统的艺术批评和历史理论更多的是和文学戏剧批评与史论融合为一的。从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刘熙载的《艺概》,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这些文论和顾恺之的《画论》,谢赫《古画品录》,荆浩的《笔法记》,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米芾的《画史》,董其昌的《画旨》,和石涛《画语录》等是互为表里的。中西的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理论虽然走的是非常不同的路子,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唯有有统筹全局的哲人头脑,对文史哲诸学科的精通,对文化发展的上下文有精准的把握,对当代文化有强烈的敏感和积极地参与的人才能担当起建树批评和历史方法论的大任。
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的错综复杂不要说一个局外人会有“雾里看花”的感觉,即使“身在此山中”的国人也常常觉得无法把握,要么失之片面,要么大而无当。比方说,“前卫”这一西方描述现代主义艺术现象的术语为何一直被1980年代及其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所使用?中国的行为艺术为什么始终保持着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而“长盛不衰”?它和西方几十年前短暂出现的行为艺术有什么不同(美国艺术家现在也还会做表演,但是“行为艺术”在此已经变成了一种“体制化”了的艺术样式)?中国的当代艺术有没有一种真正脱离社会性的“美学自律”?或者说中国当代艺术中有没有真正的“形式主义”一支?这些问题似乎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回答或解释。一种能够把握全局而又能在流派,趋向,课题,个案的分析上进行具体操作的特定的理论架构和话语体系就是一种必需了。这种体系需要结构性的创造,叙事模式的构成,也需要范畴的界定。这不仅需要哲人般的头脑,国学和西学的深厚学养,更需要对当代中国文化和艺术脉动的洞见性准确把握。我觉得高名潞在《墙》展的努力是建构这种体系的令人欣喜的开端。
分析中国当代艺术,首先需要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高名潞在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后,提出了他的“整一性”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首先是根于对多年来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艺术批评的反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九十年代初期“政治波普”的批评。基于1989年的事件和其后的政经形势的变化,人们很容易将“政治波普”解读为对政治气候左转和转趋保守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且作品只能辗转运往国外展出的事实更加强了这种解读的“说服力”。高名潞则在他1995年的“媚俗•权利•共犯——政治波普现象”一文中指出“政治波普”在讽喻毛泽东的神话乌托邦的同时,对毛话语力量本身的崇拜和借用。它在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结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身处于与这种意识形态乌托邦的共犯结构中。在《墙》展图录中,高名潞进一步分析了“个人与集体”(或“个人与社会”)和“男性与女性”(或“男权中心与女性主义”)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指出了二者更为复杂的依存甚至互相转换的关系。
从这种分析出发,高名潞勾画出了不同于西方现当代艺术的中国当代艺术图景:在西方具有美学与政治分离二元意义的“前卫”话语被中国当代艺术赋予了美学与社会意义的一元整合性。他认为,在西方,“前卫”及其相关的“现代性”有一对分离乃至对立的范畴:“政治前卫”和“文艺前卫”;“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二者分别以十九世纪圣西门的社会乌托邦学说和波德莱尔的艺术前卫理论为发端。前者以社会政治的革命和现代化从而培养出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为己任,后者则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资主义的现代性和媚俗文化相抗衡。而独立于“政治前卫”之外的在一种美学自足体系内发展的“文艺前卫”在经历了以形式主义为主轴的发展阶段——至上主义,抽象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极少主义等等——在七十年代逐渐式微,原因是后现代主义的“波普”意识取代了与大众疏离的“精英意识”,纯视觉的进化逻辑被“挪用”,“片断”,“去历史化”,“视觉拼贴”的后现代主义的“反逻辑”的逻辑所颠覆。
反观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却呈现出政治与艺术,社会与审美的整一性。对周遭人文环境和文化精神性的关切一直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整体性课题:从早期的“决澜社”,到七十年代末的“星星画会”,“伤痕绘画”,“乡土写实”,八十年代的“八五美术运动”各个群体,直到九十年代的“新生代”,“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等无不如此。甚至外表上接近“极少主义”的抽象作品(高名潞界定为“极多主义”)也不是独立于精神意义之外的“形式自律”。而胡适所谓的“此时,此地,此真理”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信条则可以看成“当代性”的原则,因为它始终关注的是人的价值选择和环境的一致性。时间永远是此刻而非线性的历史时间,空间则永远“在场”。我觉得要在此指出的一点是,“整一性”方法不是否认“二元”范畴的存在,而是强调“二元”的可互动,可互为因果和可转换关系,而扬弃一味将“二元对立”绝对化后用以分析当代文化和艺术的“方法论”(如果这也算得上一种“方法论”的话)。在段君的文章中,他引证王南溟(或者是他自己)的质疑,“中国的现当代艺术是否总是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如果有不一致的情况存在(这是无庸置疑的),那么我们还能将社会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统而笼之来对待?”这里提的本身就是个虚假的问题:细读高名潞的图录,我没有找到任何一处关于“整一性”就是指当代艺术和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说法,从“整一性”方法论的逻辑看,也不可能得出这种结论。如上所述,“整一性”是指现当代艺术对周遭人文环境和文化精神性的一如既往的关切。它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既不是同质的“一致性”,也不是一刀切的“对立性”,而是互动性,这点在“政治波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高名潞称之为“共犯结构”。
以此种“整一性”方法梳理中国当代艺术,我觉得大的图景变得明晰起来。比如,前卫生存空间的变迁就走过了征服政治空间的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以及后撤到“画家村”和“公寓艺术”的1990年代,一进一退体现的是政治与艺术的互动,环境与艺术家的共生关系。而对生活现实的真实性的追问与现实主义美学的结合则造就了前卫艺术中的社会现实主义一支,从人道,人文到人态(个人生存状态)的关注点转移,艺术家在其中建立了自己对现实的理解的方法论。而二十年的“观念艺术”从“理的陈述”到“物的自语”,其“反艺术”本质不是艺术自身逻辑的展开,而是对产生艺术的外部环境的整体性反应,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被模糊了,逻辑让位于体验,视觉与文本(观念)水乳交融。至于行为艺术,从“公共身体”,“‘受难’身体”到“‘私有化’身体”,身体这一媒介总是从属于社会,群体和所在的环境,其“仪式化”特征也正好体现了个人与环境(社会),当代与传统的交互作用(庆典,宗教,祭祀,葬礼等传统仪式气氛和符号俯拾即是)。而九十年代兴起的女性艺术,以高名潞的思路,它首先是女性艺术家与九十年代艺术大环境的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在几乎所有的当代艺术家那里都存在,而不仅是单一性别的艺术倾向。中国当代女性艺术侧重于两性身份地位的和谐转化,而性别身份问题仍与更普泛的人性,人权,现代性,个人和家庭问题纠结在一起,并未独立出来成为西方式的女性主义话题,因此女性艺术里的和谐,自然和内省的特点和西方女性主义艺术的对立对抗特征形成了明显的区隔。
至此,“整一性”方法的大结构基本成形。而高名潞在这个大结构下采取的叙事模式则是主题性叙事模式。这种模式也许不是一种创造,关键在于主题的选定和开掘,因为主题是个可大可小,可表面可深入的东西,端看选取者视野的宽狭和立足点的高下。高名潞选取的主题,从前卫生存空间的变迁,到社会现实主义,从观念艺术到“人妖同体”的行为艺术,从长城在重构历史记忆中的作用,到都市社会空间的演变,以及从“边缘人”到女性艺术,不仅一以贯之地以“整一性”方法逐一述说,而且相当精准地把握了中国当代艺术和文化的脉动。尽管在具体的描述分析时艺术家或作品会有重叠的问题,但这并不损害总体图像的准确与清晰。重读他主持写作的《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我们发现他把“理性之潮”,“生命之流”和“后85反艺术”的主题作了调整,拆解后分别纳入了生存空间变迁,社会现实主义,观念与行为的主题之下。因为在1980年代写同时期的艺术,和在二十一世纪看当代艺术的发展,视角,思路和上下文都不一样了,主题的选择调整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最后,如果我们把方法论视为一种话语体系的话,“整一性”原则构成了这一体系的基石,主题性叙事模式则形成了体系的网络架构,接下来就是创造修辞(或范畴,或模板)的工作了。有了这些修辞才能一则贯彻“整一性”的大原则,二则把主题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叙事。高名潞在批评界中有“造辞大师”的雅号,就是指他建立范畴的独特功力。在1980年代,他创造的“八五美术运动”一辞就准确地概括了那场在当代艺术史上“风起云涌”的运动,和他后来把艺术和政治,艺术和文化,艺术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来研究的思路一脉相承。他的“理性绘画”一辞也广为艺术家和批评家接受而成为研究八十年代现代艺术的“关键辞”。如上所述,“极多主义”是高名潞推出中国品牌的最明显的努力,它的英语对应辞“Maximalism”与“Minimalism”有同工异曲之妙。要点在于每个修辞的能指和所指间的精确契合及其有力的理论支撑,否则便容易流于不着边际的“玩弄辞藻”了。如前所述,《极多主义》的展览和图录为这一修辞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和理论的支持。
在《墙》展的图录中,高名潞创造性地使用和借用了一系列的“修辞”来解说错综复杂的当代艺术现象。比如“公寓艺术”这一范畴,在他的解释中,一方面是前卫艺术从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向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后撤,另一方面又是观念艺术从“理的陈述”向“物的自语”的演进。奉“日常即为观念”的艺术家或以“测量”为操作方式,或以“过程”为核心概念,创造出只在有限空间呈示的热衷于探究具体事物在一个生活环境的中介意义的观念作品。而“社会现实主义”的修辞则是对描述二十世纪早期以美国“大萧条时期”前后出现的以“垃圾桶画派”(Ashcan School)为主的流派的术语的借用(也有美术史家把十九世纪法国的米叶和库尔贝等划归为“社会现实主义”)。高名潞借以描述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当代美术中运用写实手法创作的绘画,并将其概括为“人道(人道主义)”,“人文(人文精神)”和“人态(个人生存状态)”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对所谓的“真实”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取向和关注点:当“人道”再现真实人生时,“人文”寻求理想真实,而“人态”则消遣片断真实。
而对“墙”这一建筑实体术语及其隐寓性延伸的创造性运用则是高名潞实践其“整一性”方法论从而进一步推出“中国品牌”的大手笔操作。在展览及其图录中,“墙”既是一种叙事模式,也是一个话语修辞。
早在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位置(或“立场”):东亚文化批判》季刊(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2004年冬季号中,高名潞就发表了他的“当代中国艺术中的长城”(The Great Wall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一文,阐述了他对所谓“长城话语”的产生和中国当代艺术家以一种旣爱又恨的情结用长城这一象征符号进行再创造的历史性认识。在《墙》展图录中,他将此文进一步发展成了该书第六章“重构历史记忆: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中的长城”。根据他的研究,长城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特殊地位是在193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抗日战争的民族危机和流血现实使得长城进入了中国视觉文化创作的视野。自此,长城作为一个符号的能指被不断地赋予了不同的所指意义,换句话说,其图像和含义被反复地重构和解释,进而使得这种不断解读本身成为塑造和重构中国现代性与文化身份的一个过程。在他看来,无论是“观念21”在长城上的行为,郑连杰在长城上做的“大爆炸系列”,还是徐冰拓印长城的“鬼打墙”,都是呼唤民族魂的“哀悼记忆”;而展望以不锈钢复制的长城砖“修复长城”的作品“镶长城”,和蔡国强以火药及其爆炸制造的“火龙”将长城“延长一万米”的巨制,则是“重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身份”的“修复记忆”。历史记忆和当代诠释的结合是当代艺术“长城品牌”的底蕴。
从长城推延开来的“墙”作为一个范畴界定了以“墙”为材料,客体或媒介进行创造的艺术,而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它的多重隐喻可以运用到不同主题的描述和分析。比如在分析前卫生存空间的变迁时,高名潞就指出跨越艺术与社会这堵墙成为当代艺术实践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墙”在此就是“边界”,边界的被划定,模糊或跨越构成了当代艺术的一道风景。而在“女性艺术”中横亘于两性之间的无形之墙,在他看来不是进攻与防守之间的屏障,而是两性身份地位转化的媒介,而且在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政治之墙前,两性是处于同一战壕而与后者同时进行互动的。因此,“墙”的分离,分割,障碍的寓意在他的“整一性“方法论”中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中介,联接和沟通的意义。
展览里的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墙”发生着关系。最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是徐冰的“顶天立地”的“鬼打墙”,谷文达以头发制成的“长城砖”垒出的“烽火台”,以及展望的成千个不锈钢器皿和不锈钢假山石组建的“都市风景”。虽然不止一次从各种媒体上见过“鬼打墙”,但是亲临其境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这个具有强烈祭奠效果的“巨制”占领了阿尔布莱特——诺克斯美术馆最大的仿希腊神庙的展厅(这两个“虚拟”古老文化的并置似乎有某种暗示),把长城这个符号转化为了一座纪念碑,在这座“无字丰碑”中承载的是中华民族沉重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而拓印制作付出的巨量重复乏味劳作一方面有着“极多主义”的过程意义,另一方面也象征着重复性历史的厚重感,沧桑感和悲剧性。比较而言,谷文达题为“100,000公里”的头发“长城”感觉上更像葬礼,周遭悬挂的“发帘”好似祭幛,当中的“烽火台”则有如坟冢,头发砖渗出的一种特别的气味强化了阴森的气氛。人发所代表的个人和集体与“烽火台”代表的历史互为表里,既是对历史的哀悼,又是对当代的反省。展望的炫目的“都市风景”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或者说“荒诞感”,虽然非“墙”而是“城”,但中国古典建筑体系里二者的互相依存和可转化关系(城由墙圈定,墙依城而存在)也使得这座“不锈钢城”具有了“墙”的意涵:在城市化风潮的席卷之下,原本就是“人工山水”代表的“假山石”再次被不锈钢代表的工业文化所异化,自然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墙”在城市化中被转换成幻觉和迷宫般的“虚拟现实”。这件作品使人想起了刚果艺术家博迪斯•金格勒兹(Bodys Kingelez)在2002年第十一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展出的“幻影城市”(Phantom City)—— 以纸板,有机玻璃,瓶盖,锡纸等建筑和日用品材料为媒介以艺术家对刚果首都金沙萨的观察为基础建造的光怪陆离的“城市建筑模型”。同样,刚果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面对着现代化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和协调问题。金格勒兹构造的这个花里胡哨几近俗不可耐的“幻影城市”无疑是对那种在城市化过程中不顾自身文化脉络而简单模仿“现代建筑”和“现代城市规划”的夸张的讽喻。其荒诞感和展望的“不锈钢城市”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展望作品里的有意植入的传统因子使得张力更明显,而反讽因历史的介入而更显沉重。
在展览中再一次看到丁方的作品,让我有些吃惊然后又有些释然。丁方作为“八五美术运动”中“理性绘画”的代表之一,曾经以其“城”系列和其他以黄土为主要符号的作品获得过“崇高”美学的赞誉。他曾经写过“城:文化反思的象征”一文阐述他对“城”这一符号蕴含的深重历史内涵的理解。这种深厚的历史感在他的画中一直延续到了今日,在今天的“当下”“片断”“支离”的“断片美学”中显得格外突兀,因而他被高名潞称之为“当代边缘人”。我从他的画中看出了越来越多的安森•基弗尔的感觉(尤其那幅“城系列:沙尘”),这让我有种格外的惊喜。他对自然环境的恶化与精神荒漠的逼近有种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和他在八十年代对民族文化危机的关注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如此,他与基弗尔在精神上越来越近:二者都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民族的文化身份和传统,以及人类的苦难和孤独,前者的滚滚而来的沙尘暴和后者的被烧过的犁过的土地都是民族的精神苦难的象征。
综上所述,《墙》展把“墙”这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都“最大化”了:一方面以种种不同的视觉样式出现,另一方面所指的意义也变得无穷地丰富起来。它是高名潞以中国品牌和中国方法相互支持而向世界推出当代中国艺术的一次有益尝试。品牌的认可需要时间,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需假以时日的检验。不过,它是我迄今所见最有力,最准确,最全面的一次方法和品牌并进的努力。在我看来,也许高名潞还需要在“整一性“方法论的历史线索上和中国人哲学思维的传统上进一步深究,从而使这一理论获得更有力的历史和哲学的支撑。关于方法论建设,我很赞同段君文中最后一段的态度,
“高名潞的这种理论建构态度,对于更远的中国未来来说可能更具有启发性:中国现代性处于何种情境逻辑之中的问题是一个迟早要解答的疑问。重要的是,高名潞这一代有着宏大理想的批评家一直是在试图摆脱强大的西方话语叙事,通过提出自己的独特理论————哪怕需要各方面更为残酷的检验,不断地修正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某些方法和切入点,揭示其在解释中国具体问题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以便更准确地理解和更有效地解决中国当代社会和当代艺术的现实问题。”
不同于段君的地方是,我觉得方法论的建设意义在于未来,更在于现在,一方面是推出中国品牌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批评自身的需要。严格说,没有方法就没有批评,经验性的评论也不是真正的批评。而从长远说,我们不仅仅是要“修正”西方理论,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中国的理论,从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中生成而反过来可以准确解释这种文化和艺术的理论。如果说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已然卓然有成,我们的批评却显得滞后了。批评的滞后说到底是方法论的滞后。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践行,批评界需要的就不是棍棒而是掌声,不是误读后的挑剔,而是仔细研究后的建设性批评。同时,如果能有更多的国内同行加入方法论探索和建设的行列,而不是高名潞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中国品牌和中国方法的建立就指日可待了。听说最近国内的批评有所谓的“社会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表现了一种批评的醒悟。希望这种醒悟带来的是新批评方法的“群雄并起”时代。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