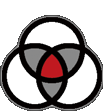|
现代性的中国逻辑:整一现代性 |
现代性的中国逻辑:整一现代性
高名潞
提要
一、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推动时代的价值观和原理。不存在普遍的现代性,现代性永远处于实践、历史发展中,现代性的本质不同文化的对抗,是空间和时间的错位,现代性也是一种历史叙事的方法论
二、西方的两个现代性(modernity) 与中国的“整一现代性”(total modernity)
西方的现代性是社会与美学二元对立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是整一的,是时间、空间、价值选择三位一体的现代性,是空间现代性,不是线性时间的现代性
三、从整一现代性的角度重新梳理二十世纪的艺术史
美学和政治前卫的壁垒并不存在,但是,二十世纪占据主流的庸俗社会学叙事遮蔽了那些看似纯审美的现代艺术
一、什么是现代性?
对“现代性”这个问题在西方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国内从90年代起在先在文学界, 然后在美术界也有一些讨论。2003年我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的整一现代性的文章,引起了一些讨论,有一些不同意见。这是好事,但这个问题还一直没展开过,我也正在写这方面文字,希望能把它完整阐释出来。
现代性这个问题跟后现代主义、当代主义不同,它不单是一个历史性和时间问题。 在国际上,它仍然一个热点。我去年12月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名字就叫“多样现代性”,它也是下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1]2004 年11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也召开了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国际研讨会。世界各国包括欧美、东欧、中国、印度、非洲等国家的批评家、理论家、策划人都参加了讨论。所以,尽管现代性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了一个多世纪,但是今天仍然在讨论。同时,今天它不仅是西方的问题,更是全球化形势下的非西方国家的所面临的问题。[2]
有的人把现代性(modernity) 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对立起来,认为它是一个时间概念,好像现代性谈的是过去的现代主义(modernism)的问题。实际上现代性是指从人类进入现代这个时期起,每个时代、每个文化区域都一直会面临的问题。目前有的学者试图将其置换为当代性(contemporaneity),实际上它们说的是一个意思,只是人们比较习惯用modernity(现代性)这个词。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性不是线形时间概念,它是一种价值观和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区域未来发展的内驱力。它如同一种原理,这种原理能带动或引导一个文化区域,并对其文化进行整合以适合其发展。所以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现代化是不一样的。
现代主义有其具体的文化意识形态、流派、艺术运动等,它是在现代性内驱力推动下所产生的具体的、物化的文化艺术现象。它可以体现为很多主义,如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野兽主义等等。我们应当注意,但我们讨论现代主义时。我们一般都不把它们叫流派(school),而叫运动(movement)。这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强调与传统、过去的断裂,强调一种造反性、背叛性 、反抗性。不再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那种流派性的艺术样式,而是以观念为主导的协作式的创作形式。如我们称“达达主义”流派而叫达达主义运动;西方最早的现代主义的标志浪漫主义运动也很少被称作浪漫主义流派。所以说,现代主义有其特定的文化形态,相对比较具体。而现代性则是抽象的、更为哲学化、原理化的东西。再有我们常提到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词其实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它是跟全球经济的重新整合和扩张相联系的。有人将现代化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阶段,它从发现新大陆开始,体现为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文化殖民;二是冷战阶段,即两大阵营的对抗,是政治意识形态阶段;三是全球化阶段,即全球经济扩张整合阶段。 因而modernity(现代性)、 modernism(现代主义)、 modernization(现代化)三个词的意义是不同的。
在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上,我提出了“整一现代性”这个概念,作为中国现代性的特点。有人批评说,不应当寻找中国的现代性,认为应该找到一种普遍的现代性,作为未来发展的普遍的价值性的东西。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现代性,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民主体制。 并认为一味强调本土的特点,是放弃了对普遍现代性的选择,即对民主价值的选择。
首先,我认为,现代性不可能是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不存在完全普遍的现代性。包括在西方内部,它也是多元的。如有美国、加拿大、北欧、西欧各自的现代性。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个人主义是民主的基础。只有到了美国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主义必须以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小单位为基础。这个小家叫nuclear family,即三口、四口之家,是美国人真正价值观的体现,即任何事都是以个人价值出发。而到了欧洲,在意大利、法国等可能就不同,它们有些东西和中国的亲缘家庭family,或社群 community的概念比较相似。美国是最典型、最极端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的体现。美国的社会保险比起北欧、加拿大等地相比差很多,对人的生活的保障相对差些,要异化一些。但从现代性的另一角度如时间就是金钱,科技就是进步,社会永远由科技推动向前发展这个方面看,波德菜尔就认为在社会现代性方面美国最为典型。因而现代性在西方也不是一元化的,我们不可能拿一个完整的现代性来作为我们的普遍的现代性的模式。西方的自由、理性、科学等现代性价值是在法国启蒙运动时确立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时期也是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盛期。所以,把现代性置入特定的西方历史时期全面地看,就会发现,这里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普世的现代性。整个现代现代史是与血腥、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将西方的东西理想化,拿来作为我们的抽象的价值模式是行不通的,那样就会掉入全球主义、西方现代性中心的窠臼。因为迄今为止,对现代史、现代性的描述,在哲学上、艺术、美学、历史、文化上都建立在西为传统的哲学话语之上的。而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时间段的划分也是从法国启蒙运动开始的才出现的,并且被用此模式来解释任何区域的人类历史。不注重在地性、区域性、文化特殊性就会掉入新的霸权主义中,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找到中国自己本土的现代性、自己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我们得把自己过去现代史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进行清理和描述。如若我们不知道自己站在全球结构中的哪个方位,就会失去自己的发展方向。
第二、现代性是实践的、历史的、发展的,不同地区的现代性不同。
如日本,它的现代时期从1968明治维新、全盘西化就开始了。而中国虽然19世纪中期也开始军事现代化,购买坚船利炮,跟着第二阶段的政治现代化,如百日维新,以及后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的第三阶段的文化现代化,都是中国早期对现代性的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毕竟是一代代人的探索和努力的结果。尽管,中国的社会的现代性程度不尽人意,但是,我们如果全盘否定中国几代人的探索和努力,用一个普遍抽象的西方现代性去衡量中国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就会对中国自身的文化基质和现代性起步的历史环境视而不见,从而陷入现代性虚无主义思维模式之中。文革之后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实际上市是中国现代性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延续。一直到今天我们仍在继续。但是经验主义很容易滑入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尊重实验,但是它的目的性方向性稳定。但是实用主义往往急功近利,只图眼前利益。这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中屡见不鲜。
若说中国有一百年的现代历史,马来西亚在60年代与新加坡分裂后,才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它真正的现代性身份、现代历史开始不到50年。要想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即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来审视马来西亚的现代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从马来西亚自身的实践、历史特点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再如非洲或英属殖民地印度等等,也不可能用西方模式来看,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在地特点。另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20世纪以来现代艺术、前卫艺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并非几条单线发展,而是交错混杂的。如在怎样看待30年代中国出现的前卫艺术与当时毛泽东延安艺术的关系上,并非如我们现在简单划分的现代艺术史的阶段性和特点那样,好像早期前卫艺术和集权艺术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因而我们必须具体地、历史性地、实践性地看待现代性的问题,而不能从一个唯一的、机械的、抽象的、完全普遍性的西方中心的角度去看。
第三,那么什么是现代性的特点? 现代性就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
如果我们超越欧美自我中心的现代性的局限,我们就必须从全球多元文化的角度去讨论现代性。于是,现代性是在多元差异的文化之间的互动、对话和对抗。就是说,从来没有一种稳定的、抽象的现代性。现代性在实践中、现实中永远是时空错位的。中国从19世纪开始直到现在始终是在和西方、国际在一种“我看他、他看我、我看他怎么看我”的关系中去调整自己的现代性和现代身份的。在这种错位中,在中国艺术中有很多表面看与西方很像的东西,实则完全不同。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女性艺术、以及中国的“现代主义”,比如中国极多主义为例,它像西方的极少主义,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就是在错位中出现的现代性,在国际与在地、我与他者之间不断错位。
再如80年代初中国的建筑进入现代时,在建筑界谈的不是现代主义,一开始谈的就是后现代主义。按理说打开国门后应先面临现代主义,如60年代的包豪斯及包豪斯之前的构成主义,可奇怪的是中国建筑师、理论家都在讨论后现代主义问题。到了90年代,全国各地却大量出现包豪斯图纸中出现的现代主义的典型方盒子建筑。这在欧洲、美国都很少见,除了到特别的科技城才能见到这样的建筑群,如MIT麻省理工的建筑就很现代,也是为了体现其科技主题,而在哈佛就都是非常古典的英格兰式建筑。全世界少有像中国这样全面的将包豪斯、现代主义、功能主义的方盒子建筑一片片地推广的,这也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在90年代才出现现代主义,80年代出现的却是后现代主义,这就是一种错位。这不仅体现在的中国都市设计方面,也体现在时装、室内设计等等领域。比如说宜家家具,在美国非常廉价,一般都是刚刚工作的小两口、大学生、研究生才光顾,因为它很便宜、实用,适合放在不大的公寓或者小房子里面。但当他们结婚生子住进独家独户的house后,大多不会买宜家,而会购买欧式的古典的家具。可在中国,宜家的购买人群不是穷学生之类的,而是中国新兴的、正在致富的中产阶级。这种错位随处可见,为什么当现代主义在西方成为廉价、批量性的东西时,在中国却成为一种高尚的、新兴的、有价的东西,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趣味,这是我们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二、西方的两个现代性(modernity) 与中国的“整一现代性”(total modernity)
1、西方的二元现代性
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前卫与现代是一对孪生子。但是,西方理论以两分法来解释“现代性”和“前卫”的,即有两个完全相反的“现代”与“前卫”概念。西方理论中,政治前卫(political avant-garde)对立于文艺前卫(artistic-cultural avant-garde,如Poggioli所说),或者社会学前卫(sociological avant-garde)对立于美学前卫(aesthetic avant-garde,如Burger, Calinescu和Habermas所言 )是最权威和流行的前卫描述和阐释理论基础。根据这一学说,政治前卫的先驱是乌托邦社会学家圣西门(Saint Simon)。他首先将“前卫”这一军事术语用于艺术,主张艺术家应同战士一样,在社会政治中扮演者冲锋陷阵的重要的角色。[3]而艺术前卫之父(或者现代美学之父)则非浪漫主义旗手波德莱尔莫属。波德莱尔提出了一个新的艺术方向---审美的现代性,以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质主义的现代性相抗衡。这种物质主义的现代性主张进步,科学高科技、高消费﹑时间的可计算性等等。它的代表即是中产阶级的媚俗文化。相反波德莱尔的美学现代或者美学前卫则主张艺术家疏离或自我放逐于这一中产阶级物质化社会之外,在象牙之塔中去寻找真、善、美。这种有关现代和美学前卫的描述或多或少地受到青年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理论的影响。[4]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阐述,由存在主义继续发展,而最终由后现代主义理论所继承,比如,当代流行的“文化产业”的理论(cultural industry)。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常被西方学者用来描绘现代主义者,尤其前卫艺术家们,称他们为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颓废的少数派。这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前卫理论也是建立在两种现代性的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的。由此推论,正是资本主义的异化造就了前卫艺术的象牙塔,而在这座象牙塔里,艺术家们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批判的现代主义艺术,他们被标榜为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和大众流行文化格格不入的精英艺术。[5]
自此,美学前卫就成为西方现当代艺术词典中的词条,其主流地位不可撼动。很明显,美学前卫是伴随着审美的现代性诞生的。如哈贝马斯所言:“19世纪出现的浪漫主义精神激发了现代性的意识,而现代性意识将它自己从重重的历史束缚中解脱了出来。而这个才刚刚过去的现代主义不过加倍地掘宽了传统与现在之间的鸿沟”,而我们(西方人),如哈贝马斯所言,“从某种程度上讲,仍然与那个刚刚逝去的美学的现代性处在同一个时代”。[6]
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认为,美学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分野,就是最初由法国启蒙哲学家所倡导的社会现代化工程的结果。[7]这项社会现代化工程,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那里亦被称作“理性化”(或工具理性)(rationalization)。韦伯认为文化的现代性的特征是将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内容肢解为三个独立的领域,即科学、道德和艺术,而每一个领域都由此领域中禀赋异于常人的高人专家掌控。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专家和大众之间的距离拉大。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分裂导致了不同领域专家之间的独立、疏离以及学科话语的形成。而正是康德的美学和黑格尔的三段论的美术史学将美学和艺术从传统哲学和神学中解放出来。才有了现代西方艺术史学和批评的诞生。而正是这种诸学科、思想领域之间的分立/疏离,奠定了现代西方对于审美现代性和美学前卫的研究的哲学和史学基础。[8]
总之,西方前卫和现代性理论向我们展示的是二元论的一幅画面。其中,政治前卫只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是反审美的;同时审美前卫只追求“为艺术而艺术”——一如当初波德莱尔在19世纪中所首先倡导,并此后成为20世纪前40年的“正统前卫”(canonized avant-garde),或者“历史前卫”(historical avant-garde)运动的主要推动力。这种纯粹视觉革命的动力造就了我们所说的西方现代主义。而它的代表学说就是Greenberg 的现代主义的“艺术是艺术本身”的艺术进化论。艺术的高度独立自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之始科学、道德、艺术分裂的衍生物。
而且,美学的前卫亦伴随着一个主导思想而来的则是反艺术和反传统。因为美学的前卫的哲学理念是把自己限制在艺术形式的独立发展和革新的历史逻辑之中的。
西方学者讨论现代性的角度
当西方学者讨论历史和文化的现代性的时候,有的人是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去谈什么是现代性,以区别于中世纪。这体现在对现代历史的起源和分期问题方面。但很多学者把现代性当作一种方法去描述西方的历史,如思想史、现代话语史等等。如哈马贝斯在他一篇的文章里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他提出是从词语的角度回溯到公元四世纪到公元五世纪,在那个时期,“现代性”这个词就已经出现,但当时“现代性”这个词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现代性”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反叛、前卫、反传统、反权威等等。但在中世纪早期及公元一世纪到五世纪时,这个词在西方用时和基督教有关,当时的基督教要转化成罗马官方的宗教,必须把自己正统化,而要正统化就须回溯到历史。所以modernity和modern就与基督教的起源、正统有关,它和我们现代人理解的“现代”不同,我们的“现代”指反传统的面向未来的价值标准,现代人就是未来的“候选人”,是过度人。哈马贝斯从历史这一角度,把西方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一直到浪漫主义时期,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再到法国启蒙时期是怎样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去描述。而韦伯则认为现代性具有现代工具理性。西方开始出现现代性时,宗教、科学、艺术三元分立的结构造成西方的社会性和美学性这个二元分立的现代性的发展。韦伯的知识极其广泛,他把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也进行了一番清理,试图找到不同的文化区域在面临现代性时,其传统结构能否转化,怎样转化,他试图从文化结构这个角度去解释现代历史,解释现代思想史。
艺术史的现代性讨论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些学者和艺术家主要集中在美学和艺术本体的问题之上。比如,早在19世纪中的浪漫主义时期,波德莱尔认为,西方的中产阶级的媚俗已经到了一种不可容忍的阶段,到了一种必须要进行批判的阶段。他提出了几个观点,一是现代是一种瞬间,我们必须尊重现代是在变化的。而且现代是现代人的生活,现代的艺术不应该是这种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庸俗大众的趣味。丑的也可以是美的,原始的也可以是现代的,这是浪漫主义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反社会现代性的现代成为一种艺术和美学的现代性,这在波德莱尔成为一种现代艺术的价值判断。浪漫主义强调直觉性、非理性,和资本主义提倡的进步、科学、理性、时间可以由金钱来计算等等,提出原始主义非理性来反抗现代主义的工具理性,他促进了浪漫主义艺术、文学的出现。还有就是格林伯格。他从美学现代性的角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方启蒙主义运动,到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艺术、美学如何进化的角度讨论艺术的现代性。他认为进化和革新就是回到艺术本身,媒介本身,这导致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出现。他这条线路的描述是完全站在西方美学、哲学原理的角度进行的价值判断,当然也和美国的文化战略、价值观、国家利益是紧密联系的。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社会现代性的角度讨论现代性。比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T. J. Clark ,他是60年代出现的一位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历史学家,在70、80年代影响很大。他写的最早的一本书是关于库尔贝的,他写库尔贝在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后作为前卫艺术家怎样创作他的艺术的,以及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是怎样影响到他的艺术的。他紧紧抓住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整合马克思原来的原理和美学进行嫁接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第二本书是《现代艺术与现代生活》,是描述关于后期印象派的书。他描写的后期印象派和我们了解的不一样,中国一开始接触后期印象派的时候,是从纯粹的形式主义角度去理解,如光、色等。但T.J.Clark不是这样描述的,他把后期印象派的创作看作为当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巴黎这个都市从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这个转化过程当中,伴随而来的是它的现代都市景观的明显变化。这种景观,不仅是都市的景观,它还是一种社会的人在阶层转型中的一种变化。如女人从家庭里走出来,进入咖啡馆、沙滩等更多的公众场合。很多后期印象派画家都画女人,画中出现许多新姿态的女人,女人组成了都市景观的重要部分。 T.J.Clark解释了这个现象,而他的解释不像格林伯格是从形式的、进化的、精英主义的、大师的角度去检验它, T.J.Clark是有他自己的结构方法的。T.J.Clark和格林伯格曾经在70年代有一场关于什么是现代主义的争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中国曾经把这个原理用在分析毛时代艺术上,认为经济基础决定阶级,进而影响艺术形态。但是T.J.Clark认为不能简单地用这种二元的东西去解释,他找到一种符号,他把这种符号叫做spectacle(景观)。景观和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构成三元关系。景观和经济基础有关,但是这两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复杂关系,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解释的,这一点就是T.J.Clark书中解释后期印象派所运用的基本方法。
再举例说一下关于先锋或者前卫性的问题,因为现代性和先锋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西方有两本很重要的书。其中一本是由意大利的学者,也是哈佛的教授Renado Poggiolio的著作,他在60年代发表了一本书叫《前卫理论》(Theory of Avant-Garde)。另外一个是比格尔,他的书的名字也叫《前卫理论》(The Theory of Avant-Garde)。然而,这两本书的出发点和讨论的角度很不一样,Poggiolio以历史角度把浪漫主义作为前卫的起源,并且讨论了不同的现代主义流派、不同的先锋性。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很少谈经济基础的形态,比如体制和艺术的关系。而是更侧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谈什么是前卫意识,并且将其分为五种类型。比格尔把前卫艺术的历史和描述前卫的理论话语分开,认为前卫性本身的发生是一个历史现象,它是一种存在。但用什么样的理论去描述前卫性,则是先锋理论自身的问题。所以,他的书一开始先谈方法论的问题,他先谈什么是先锋的话语,先锋的描述和先锋的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等。比格尔和Poggioli不一样,他认为现代性、先锋性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所催化出来的必然产物,这导致前卫艺术必然要产生,而前卫艺术的产生就是对它生长于其中的体制的有意识的批判。它把体制批判直接作为先锋性的内容。而并非像Poggioli或其它人把前卫的意识形态和美学现代性从那个资本主义体制中分离出来,并将西方前卫意识形态看作为异化的等同物。用审美的现代性去看前卫艺术。与Poggioli 不同,比格尔不但把体制作为前卫艺术的根源,同时还作为前卫艺术的中心内容。如杜桑的小便池在他看来是一种内容。反体制成为前卫艺术的内容,也正是因为反体制是现代艺术之前前所未有的。这就形成了我们所称之为的先锋性。换句话说,反体制是先锋性的创造发明,所以反体制必定是先锋性的表现内容。当然他的反体制不是指反对美术馆实体,他的“体制”是指艺术所依附的社会价值系统,这个系统是由宫廷、阶级或者商业化机构所建立和控制的。所以,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从所谓纯粹的思想意识方面去检验艺术的本质,而应该从艺术作品与上述体制之间的关系方面去检验它是否具有先锋性,这个就是比格尔的《先锋理论》的中心议题。
这种研究先锋性的角度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由于中国当代艺术面临两种体制,即政治体制和商业体制的杂交生态。于是就显得异常复杂。以往那种简单地从官方和反官方的角度研究中国前卫艺术的方法已经失效。从1980年代的先锋艺术现象是不能简单地以官方和非官方的二元论为评判基础的。1990年代以来,因为官方和商业无论在价值观和自身生存方面都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互动和相互置换的特点。现在中国的艺术家都忙于进入两大体制空间,而民营空间如雨后春笋出现,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体制空间的“春秋时期”。 上百个艺术空间在竞争,但是过几年会出现“战国”时期。只有一些较有实力的艺术机构能够保留下来。但是在这种体制整合的过程中,艺术的先锋性将受到重新检验。
相反,格林伯格谈论先锋性的时候,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文化趣味的角度以及视觉形式的进化的角度谈“先锋与媚俗”。 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将媚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即斯大林的艺术(他没有提到中国的艺术)。另一类是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是为大众的,大众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去思考和欣赏现代艺术,他们只能接受这种虚构的、英雄加美女的传统叙事的艺术,精英和大众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种精英和大众完全对立的叙事,在中国20世纪的艺术史中,可能不象资本主义社会的那样简单。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也正在面临这个问题:面对商业化的全面冲击, 我们要不要建立一种新的精英话语系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从什么角度以及用什么样的话语形式,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尽管早期“现代性”的精英主义的艺术理念、疏离大众的倾向已经被后现代主义的波普意识代替。纯视觉的进化论也被平行挪用传统和当代视觉资源的拼凑风格主义所彻底颠覆。而“前卫”一词,在1970年代西方对现代主义的一片声讨中已经死亡,但上述的有关两种前卫和现代性的“旧理论”仍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些西方研究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美术史专家和批评家的讨论和判断。这种二元分立的理论似乎在西方的当代艺术批评中已经没有太多的市场,但在评论非西方的特别是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当代艺术时却仍能排上用场。一个流行的说法即是,后者的前卫性应当是与正统的西方美学前卫主义有别的政治前卫。所以,前苏联的艺术被西方批评家描述为政治的艺术,并极力把它和马列维奇、波波娃和塔特林的早期前卫(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去分开,认为后者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正统美学的一部分,而斯大林的集权艺术则是另类的政治的艺术。苏联消失后,一些本土理论家对这个西方分离的理论提出了批评,比如, 波瑞斯·克若伊(Boris Groys)在他的《整体斯大林主义》一书中,把俄国的早期前卫、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八十年代的地下艺术看做一个逻辑发展的历史,互相联系和重叠的整体结构中发生的历史,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一些西方批评家也从西方二元的前卫和现代性的角度分析和判断中国的现代艺术和先锋主义。我在这里举一个较早的例子。邦尼·麦克多卡Bonnie McDougall在其影响广泛的《西方文学理论在现代中国》(发表于1971年)一书中,描述了20 世纪1920、1930 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主要潮流,并探讨了一些中国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沈雁冰等是如何受到西方前卫思想和文学运动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甚至达达主义的影响的。 [9]McDougall最终的结论是,发生在中国上世纪20、3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算不上一场前卫运动,因为当时中国的文化背景根本就不会欣赏那种正在西方成长的古怪异常的前卫艺术。表面上的影响只是出于对西方化和现代性的冲动。她所描绘的当时中国与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或许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她的评判的立脚点却是西方传统的审美学现代性和美学前卫的理论。比如,McDougall给中国新文化运动所作的结论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新文化运动中,并不是全体艺术家加入到反艺术的行列,很多人的想法还很传统。其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为牢固的传统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负所束缚,另一方面也积极投身到当时的社会活动中,因此无法真正地放弃传统,彻底革命——换句话说,他们太社会化,太政治角色化,缺乏艺术独立的思想和实践,而这恰恰是西方社会中前卫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10] McDougall的观点代表了部分西方学者对现当代中国艺术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现、当代艺术不具备充分自足的美学修辞和话语系统,这是由它自己的社会历史逻辑所决定的。即便中国有前卫艺术,它也只能被看作为“政治前卫”而非能够与西方美学前卫相提并论的它类社会现象。
然而问题是,鉴于在中国现代史上类似西方的艺术和道德宗教分立的现代性从未发生过,那末怎么能用西方的二元理论和西方的两种前卫的标准去评判、描述中国的现、当代艺术现象呢?还有,西方的审美艺术和非审美艺术对立发展的叙事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现当代艺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中国的现当代艺术,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现代性开始出现之初,艺术即被看作是中国的整一的社会现代性的一部分。它试图整合审美、宗教及政治为一个有机体,因此,它被认作是人的社会化生活的一种和谐方式,而非异化方式。
2、 中国的“整一现代性”
在中国的背景中,现代性和前卫的概念不是二元的,是时间、空间、价值三位一体的现代性;现代性在中国意味着新的民族国家,更多的是空间意识,而不是时间意识
所以我试图可以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叙事方法,同时也找到一种所谓中国现代性的特点去描述中国现代意识。我发现中国的现代性不像西方的二元分立,它是三位一体的,是时间、空间、价值的三位一体的整一性。
与西方的情形一样,是现代意识促使前卫主义文化艺术出现。然而与上述的西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历史逻辑的延续性和现代性的西方中心主义不同,在中国的现代历史的初始阶段,现代化的工程就不是分裂的,而是一个整体。中国人并不寻求建立在艺术、道德和科学分立之上的艺术的独立和自主,而是将各领域整合:艺术、宗教和科学都需要为一个最优先的前提服务,即民族自强和如何赶超西方现代文明。另一个特点是,一百多年来时时困扰着中国人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逻辑是如何彻底地切断它本身的历史时间线性的逻辑性,追求彻底和过去的价值观断裂。第三个特点是,强烈的新民族国家的意识导致了一方面在思维空间上不断试图打破传统的地域疆界的园囿(反传统),而另一方面则又体现了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的反殖民主义倾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虽然在二是世纪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但是,每当激进的现代化思潮出现时,长城和黄河必定成为一个批判保守主义的象征靶子。比如鲁迅和80年代的《河殇》对长城的激烈批判,电影《黄土地》对黄河的哭诉与《河殇》对黄色文明的批判和对蓝色文明向往是一致的。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相比,其实是最反传统的、最暴力的和最彻底地打破历史逻辑时空的现代性。西方的“反传统”其实只不过是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另一种西方的权威说法是从17、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开始)艺术人文、新教伦理、和科学革命的逐步发展所造成的自恋式的形式化描述而已。而在实质上,西方的现代性其实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宇宙中心主义的合逻辑的发展,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合逻辑的结果。[11]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与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形成和完成的过程是一体的。但是,中国的现代性必须得在尽最大可能整合所有的文化方面和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自己的现代化社会,以摆脱在“时间差”的意识表象不断形成的被动的被殖民文化身份。这就决定了我称之为的中国现代性的“整一性”性质(Totality)、它的反历史线性时间逻辑的非理性特点以及西方中心的民族主义的三位一体的特点。或许,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化的本质,同时也是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的现代性本质。
在这个整一现代性的意识的主导下,中国的早期现代艺术在三方面进行了整合。一是倡导宇宙主义的审美观,使艺术在现代社会发挥准宗教的作用。应当说,这恰恰是传统“文以载道”的现代性转化。它超越了西方的艺术独立观念。蔡元培(1868-1940),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并兼北京大学校长,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两年即1917年,首先提出了“艺术代宗教”说。[12]这显然有别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艺术、道德和科学分立的西方现代理性化的特点。蔡元培倡导艺术应当同宗教和道德一样担当起社会使命。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文艺教育应当先行。显然,由于蔡在德国留学,受到了康德的宇宙审美标准的影响,但却摈弃了康德的审美独立的核心。一些受蔡元培影响的文艺流派,均认为艺术源于准宗教式的人文情感,而这情感又是基于对中国平民身处的水深火热的境况的关怀。比如,林风眠等人提出的“艺术为人生”就是一种用抽象和形而上的形式表现人文主义情怀的艺术观。林认为艺术是情感的宇宙,而艺术的作用就在于表达某种宗教的情感。[13]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在以徐悲鸿和蒋兆和为代表的学院派现实主义绘画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在形式上与前者有很大的区别。甚至那些投身到极端的“形式主义”创作中的人,过多或少地对人的生存环境给予了关注,比如,庞熏琴 (1906-1985)、倪贻德(1902-1969)和一些在1930年创办的决澜社的艺术家的作品。[14]
二是将传统的儒家“经世致用”转化为现代的“实用主义”。因而“拿来主义”即可上升为文化策略的层面,成为西学为用的代名词。实用主义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20世纪的各类革命运动,前卫革命也不例外。在20世纪的第2个十年间,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想洪流中,实用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影响最为深广的哲学理论。胡适,1907年至1912年间他在杜克大学学习,深受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并将其介绍到中国来。胡适曾经注解过实用主义说: “真理不是别的,就是用来提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手段。人类需要的真正知识不是所谓的形而上学哲学和逻辑的绝对实质(如西方传统那样),而是具体的空间,特定的时间和我的选择。”[15] 这三位一体就形成了具体的情境化,这个情境化(context)就为经验主义的现代性原理提供了结构性和变异性的依据。它没有西方那种绝对原理化的、对立的、二元的现代性的观念。
第三是将传统士大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坐而论道转化为知识分子直接参与大众文化。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艺术革命”是由少数精英喊出的口号,它最终还是将中国传统自娱的文人艺术引导向艺术化大众的方向。最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持续有力的影响、30年代左联的积极活动以及后来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艺术的革命”彻底转化为“革命的艺术”,而“艺术化大众”也演变作“大众化的艺术”。[16]左翼文艺运动包括木版画运动和十字街头艺术家的口号非常鲜明:艺术家是社会的勇士和先驱。左联的文艺家们有意识地称自己为前卫或者先锋。 [17]三十年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梁实秋曾(生于1902年)将此类文艺创作命名为“人力车夫派”。[18]但是,左联时期的“先锋”意识还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贫民阶层的“同情”。只有当这些左翼艺术家到了延安以后,真正的转变才形成。先锋文艺由此经历了嬗变的两个阶段。首先,由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导的艺术家转向平民大众化,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从原先的“小资产阶级”脱胎换骨,转变了广大的无产阶级阵营的一员。之后,先锋文艺创作由艺术家个人对救国救民的单纯热情转变为阶级斗争条件下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从而彻底消灭了个人主义。整个转变过程中既包含有意识形态的转变,也包括身份性的转变。虽然,中国的早期前卫艺术家向社会主义革命者的转换类似于早期苏联的十月革命时期的前卫艺术以及墨索里尼政变期间的意大利未来主义。[19]但是, 30年代和40年代的中国先锋文艺的转变,却较苏联和意大利都温和及合逻辑得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30年代的前卫艺术家 --- 如左翼木刻家的现代意识并不是像苏联的前卫艺术家,如塔特林、里奇斯基和波波娃等人那样要创造一个建立在现代机械和几何图形之上的乌托邦精神。并认为这种现代形式和精神也应当符合十月革命的精神。所以有人将其称为“物质乌托邦”。[20]相反,中国的早期前卫的现代性却充满了“人文乌托邦”的因素。[21]
英文的“avant-garde”在中国文学中常被译作“先锋”或者在视觉艺术中译作“前卫”。具有军队统帅和先锋官意味的“先锋”一词,长期以来都存在于中国古代典籍当中。比如,《三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22]但直到20 世纪30年代,“先锋”这个词才出现在中国的文化领域中。那时,一些受马克思影响的作家开始引用转译自俄语的“先锋”来指代中国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文学。30年代上海左联的激进刊物之一就命名为《先锋》。在30年代以至于后来的80年代,许多“先锋”的同义语词常常被广泛运用,比如“现代”、“新潮”、“新”、“革命”等,用以指代前卫文学和艺术。[23]虽然“先锋”一词直到1932年才出现在文艺领域,但并不等于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就没有先锋的观念和实践。
我们不妨把毛泽东时代的文艺也看作为一种现代艺术类型。因为它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现代主义的衍变类型。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艺术当然是最先进的和最现代的,它代表了未来。它的未来主义、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精神是与西方的传统前卫艺术是一致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西方现代主义痛恨是源于它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品,即资产阶级颓废的个人形式主义。但是,如前所述,在同样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的现代性和前卫艺术理论中,这种颓废的个人主义形式主义却是被正面加以肯定的,被看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物,是与中产阶级的媚俗趣味不同流合污的精英艺术。在格林伯格那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中产阶级趣味是一样的庸俗艺术。只有西方的抽象主义艺术才是真正的正统纯艺术,它探讨的是艺术回到艺术本身(点线面)的艺术进化的问题。这种形式主义理论的根本在于,艺术是形式问题,并有好坏之分,而抽象形式有其内在的法则。 只有一些类似蒙德里安、毕加索这样的现代的天才大师,才能发现和表现这一法则。虽然,弗莱(Roger Fry)和格林伯格等人从理论上建树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经典地位,但它们的正统的形式神秘主义却未必反映了西方现代艺术历史的真实。因为,艺术的实践总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权力发生互动的。艺术的意义不能仅仅从艺术作品本身的形式甚至内容去判断,而应当从它与社会文化的上下文(context)之间的互动的角度去判断。比如,一些西方的批评家今天重新看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运动时﹐以各种证据显示﹐这个运动曾是美国政府资助的﹐试图以它作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国家文化的样板、国际主义的艺术主潮而操作推动的所谓的纯粹的抽象主义艺术运动。 [24]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核心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有不同的主张,比如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平庸的中产阶级大众趣味,如何去批判,阿德诺主张疏离和拒斥大众社会﹐而卢卡奇则主张艺术应反映这种现实。不论怎样,社会政治和艺术似乎总是处于对立的双方。所以马克思的文艺理论仍然是建立在西方二元论的基础上的。
虽然,毛泽东时代的艺术有中国自己的图像学的、风格学和叙事性的独特特点。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艺术理论在思维方法论方面,彻底地受到了西方的二元分立的方法的影响。一些在中国传统甚至是20世纪早期还不存在的对立范畴,如唯物对唯心、主体对客体、革命对反革命等在1940年代后期以来成为中国艺术理论的主导性话语。而20世纪初的中国的整一现代性也被推向极端。在“艺术为政治服务”中,艺术变为一个附庸,一个陪葬品,艺术和艺术家作为工具置入到所谓的“整一”的社会意识形态或体制之中。这是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整一性”现代的危险性所在。
当“文革”后,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再次成为主要关注点后,对现代性的思考和讨论似乎又返回了20世纪初的内核, 即对“整一性”的现代意识的追求。这在85美术运动中体现得最为明确。它的主导艺术观念试图超越毛泽东时代和文革刚刚结速时的政治艺术极端对立的模式。尽管它在行动意识上,如办展览、发宣言、自发组织群体和集会等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性。但在艺术观念上,艺术、政治、人性、道德、甚至宗教是被整一性地思考的。这在85运动中是一种主流追求。这种整一性现代工程的思考很象20世纪初的处于新文化运动中的艺术实践。所以,我在那时写的“85美术运动”一文中将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联系。
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通常的理解是现代即是前卫,前卫即是现代。同时,还有很多类似“新潮”、“新具象”“新野性”等现代的代名词。在1980年代,“现代”是85运动的主要用语。很多自发的前卫艺术群体用“现代”一词为自己的展览和群体命名。尽管,当时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已经进入中国,并且有所讨论,特别是在建筑界。但是,“现代”一词的运用仍是主潮。比如,“厦门达达”虽然提出后现代的观念,但是他们在1985年和1986年的展览仍然用“现代”命名。相反,直至80年代末,才有年轻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开始使用“前卫”一词。但是同时,也有如福建的“厦门达达”、广州的“南方艺术沙龙”以及“湖南艺术展览协会”认为自己是“超前卫”,或者“后现代”、“当代”。[25]艺术家和批评家开始频繁并正式启用“前卫”一词是自1989年2月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China Avant-Garde)起。此展览的中英文的不同名称的运用上,或许说明了当时我们对“现代”和“前卫”的关系的理解。当时的这一大型展览,只出版了一本小图录。除了我写的一段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一段话外,其它都是图。当时负责图录编辑的主要是周彦,侯瀚如参与了英文的翻译工作。但是,记得当时我们决定中文的展览题目叫“中国现代艺术展” ,而英文名称没有按中文的直译为China Modern Art Exhibition 而是按照它的真实原意翻译为China Avant-Garde Exhibition, 即“中国前卫艺术展”。[26]因为我们那时明显地感到,尽管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现代”和“前卫”是一回事,但是对于处在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西方观众而言,如果我们使用Modern (现代)一词会使他们误解为陈旧的过时的现代主义的东西。所以我们选择了avant-garde 即前卫一词作为英文的题目。但是,事实上,“前卫”和“现代”的概念在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西方均已经死亡。可是,1990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在国际展览和介绍中,中国“前卫艺术”的名称却不胫而走,成为描述中国当代艺术的主要名词。而前卫在中国的1980年代可能意味着“新”和“激进”,但在西方却有很明显的中国“政治前卫”的意味。“前卫”在中国和西方的错位使用正说明了文化的误读(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往往在造就某一它者文化身份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而这种误读又是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的环境紧密相连的。比如,如果仍然用西方传统的现代和前卫的理论去看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就象邦尼?麦克多卡McDougall看192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那样,大概85美术运动的艺术后也不能算作真正的“前卫”或“现代”艺术。因为,(让我们重复Mcdougall 的话),艺术家们“一方面为传统和社会责任的重负所束缚,一方面自己却积极投身到当下的社会实践行动中,因此无法真正放弃传统”,换句话说,他们太社会化,太泛政治化,既缺少艺术独立的观念,也没有艺术独立的实践。然而,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中国前卫艺术的“非艺术独立性”或者是它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反而为它赢得了“前卫”的称号。因为,它的身份可以游离于传统西方的前卫理论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系统之间。所以当中国的当代艺术面临“国际”双重标准评判之时,它的“整一”现代性的自身内在逻辑即被彻底忽略。
不论这个“整一性”好与不好,它是一个事实描述,不是凭空编造的。这种整一性是中国现代以来艺术发展的现实,但它是我概括的一个特点。 我们不能因为它不理想,它给我们带来了集权艺术的后果和媚俗艺术等诸种弊端, 我们就要否认它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种缺失的现代性,但不等于说它不是现实。 这种“整一性” 已经形成为中国本土的、不约而同或者集体无意识地遵循的现代性原理。它能在中国延续一个世纪本身具有其合理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前面说的时间、空间、价值(也就是“在地、此时和我的判断”)的三位一体的东西。因此,这个更为立体的、更为经验性的本土现代性是建立在具体“情境”判断之上的原理。“情境”不是完全物理的空间,是人的意识参与的空间,是意识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融合。所以,中国的整一现代性是有关空间的现代性,而西方的现代形式以时间为基础的现代性。所以,在实践现代性那里现代被分割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位一体系统中的极端实用主义因素排除掉,再加进更多的理想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整合成一个很好的,对未来发生两性影响的价值原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去讨论。
三、 建立在二元对立论基础上的关于两种现代性和两种前卫的叙事方法,无法阐述和解释中国的20世纪艺术现状。
在21 世纪之交,中国艺术从1980年代对人文主义的观照转向对市场和机制的追逐,是中国被纳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明证。从在本土政治和文化的现状中展开对前卫理念的追求,转向一种超越本土兴趣热衷国际战场的“准前卫”的视觉艺术是一种惊人明显的转变。如果我们关注这样深刻的转变,还把它依旧放在西方的现代、前卫二元论的视角中去审视它的话,我们会完全误解原初语境和当下全球化语境下互动中的中国当代艺术。这样的误解会导致政治和审美的错位。尤其是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关于中国当代现代性和前卫的话题变得越发复杂,中国的“整一现代性”和前卫的含义较先前更加暧昧不明。
不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讨论,在我看来,依旧保留了二元论基础上的阐述方式,用两极对立的概念,如官方对非官方、政治对审美、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等等,来阐释中国当代新艺术现象。这类二元对立的现代和前卫理论方法,显然在如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现实中已然失色,可依旧在非西方的艺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比如在中国。这并不意味着运用这一方法的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全都是西方批评家,也包括中国人自己。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曾影响我们几代人。
一个例子是如何用官方和非官方的对立来阐释政治波普。1990年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和所有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出版物,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认为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是最主要的非官方/反官方的前卫运动,是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影射批判。而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思考则表明,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掩盖了一个重要方面,即政治波普的民族主义的倾向。 这种民族主义与20世纪初和其后的毛泽东时代有某种共通性,这并不为政治波普表面形式上的政治、商业混杂造成的反讽效果所遮蔽。政治波普的艺术家(他们大多是85运动的参与者)对文革和毛泽东时代抱有复杂而矛盾的情绪。他们赞美毛泽东时代的艺术的说教力量以及它独特的美学形式。余友涵称毛泽东时期的艺术“喜闻乐见”,王子卫尊敬毛泽东关心并同情中国平民百姓,王广义崇拜毛泽东时代宣传画的印刷复制能力,尤其是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机械复制的时代。[27]尽管政治波普讽喻毛泽东的神话乌托邦和它造成的政治现实,但艺术家们决不批判毛泽东的权力话语力量本身。相反,艺术家们依旧崇拜并渴望获得这种话语权力,并以此作为一种建树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力量源泉以面对全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在他们的作品里,毛泽东本人和那个时代的艺术不仅仅被看作为政治领袖和意识形态宣传的产品,而是作为刚刚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和中国人的一笔遗产。对不少中国艺术家来说,毛泽东是真正懂得如何使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就如徐冰在他的英文书法系列创作里反复强调的。
我在1995年就曾指出,中国政治波普和苏联的Sots 艺术运动的类似性(Sots Art, 1970年代莫斯科出现的苏联先锋艺术运动 ,Sots 是socialist “社会主义”一词的缩写)。Sots 艺术也是苏维埃群众文化的和美国波普的拼和变体。[28] Sots 艺术和政治波普共享一个相类的民族主义诉求。如波瑞斯·克若伊(Boris Groys)在分析Sots 艺术时说的,“在苏联,当政治家们积极地以一个单一的艺术模式去试图改变整个世界、或者至少这个国家时,艺术家可以容易地找到他们游离的自我,不可避免地发现他们自己与那压制与否定他们的专制模式有一种共犯关系。他们发现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权力的冷酷无情竟然出自同一根源。Sots 艺术家和作家们因此决不拒绝承认他们的创作意图和对权力的渴望的主体性,相反,他们将此主体性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内容,去表现两者间潜藏的亲缘关系,而在一些人那里(主要指西方评论家——引文者),则很舒服地把这种关系看作为道德上的对立”。 [29]克若伊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得将Sots 艺术放到俄国与苏联的整体社会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中去理解,不能完全从道德的对立,即肯定或者否定的角度把它和官方艺术对立起来。事实上,二者在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是暧昧的。
政治波普比Sots 艺术更多地吸引了国际机构和市场的主意,因为它们出现在共产主义世界崩溃 和冷战结束的时代出现的,也因为此时中国开始变作世界跨国市场。在1970年代末移民美国的Sort 艺术家们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但没有一个商业上更为成功的政治波普艺术家离开中国。相反地,他们在中国日新月异的的转型的经济机构中变成高级中产阶层的一部分。这些艺术家不再像他们的先驱那样同权威者继续对立,而是由文化精英(业余前卫)转变为职业生产者(专业艺术家)。民族主义和唯物质主义为基础的政治波普,诞生在跨国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巧妙地同国际市场、国际艺术机构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共处并受益。政治波普所宣示的身份性远较Sots艺术复杂。它的背后的意义也远比它在艺术中设计的简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双重媚俗的符号暧昧得多。所以,对中国前卫用“官方与非官方”对立的简单二元论描述,在现实中是苍白和无力的。[30]这类的谬误可以举1993年12月的《纽约时代》杂志为例。内中有一位纽约时报记者介绍中国当代前卫艺术的文章。杂志封面上印有方励君的光头作品,并附有一行标题:“是怒吼而不是打呵欠,它能救中国!”[31]它显然指的是作品的意识形态可以救中国。但是,现实会是对这一结论的最大讽刺。 所以,如何界定中国的前卫在全球化情境中更为复杂。从全球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它可能是前卫的,
这种“官方vs非官方”或者“非官方vs非非官方” 的前卫叙事理论,在面对21世纪的中国当代艺术现状时,继续失去阐释的能力和意义。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体制而非单纯意识形态的代表的官方却悄悄地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要赞助人。但是,却很少有人正视这一变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所起的作用。而今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和北京的所有重要的美术馆都在争相举办国际艺术双年展。最近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中国两大最为官方的艺术机构携手承办了10月的北京国际双年展,邀请了众多知名西方艺术家和中国“老前卫”前来捧场,包括徐冰和蔡国强——他们的作品和那些“保守”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比邻。虽然预计在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露面的第一个官方的中国艺术馆因SARS的缘故不得不取消,却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原先的先锋艺术的“宽容大度”。另一方面,这类由中国官方组织同国外美术馆或者展览会联手打造的项目,也与艺术市场的关系紧密,收藏家现在甚至比批评家和艺术家对全球的展览信息更为了如指掌。所有这些同时在损毁、吞噬着中国前卫艺术的精神基石。先前的先锋艺术如今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国家现代化形象的最光彩的角儿,这形象不但为西方世界接受,也为中国官方认可。前卫艺术的弱化并不在于它进入官方的展览馆这种外形式,而在于本身的批判性和作品失去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力度。因为,在中国那种所谓的纯粹“非官方”艺术可能从来就不存在,即便有也可能是沉默的。可能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中,真正有效的“非官方”艺术必须得在与官方“共处”(或共犯)中发生意义。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即是一例。没有中国美术馆这一官方场地,该展就不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冲击力和历史意义。但是,中国目前的官方展览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却是追逐“国际形象工程”的表面热闹和繁荣,而淡化批评意识和缺乏中国当代艺术内在的叙事逻辑的清理意识和在方法论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体系化的建设。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路发展而来的中国前卫艺术就很可能在这种“繁荣的”情景中堕落。中国当代艺术在21世纪初的头几年中正发生着一种不为人警觉的嬗变,这很可能是重蹈1930年代左翼木刻运动的覆辙。中国艺术家今天面临的是前卫艺术是否死亡,或者已经死亡的问题。21世纪初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景象可以被名之为“展览的时代”。但是在这繁荣的景象中,掩盖着一种不能自拔的堕落现象。展览决定着艺术家的命运,而批评家、策划人和博物馆、画商都以展览空间作为他们成功的原始舞台。“展览时代”对旧的意识形态禁锢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另一负面效果。对此我称之为“蹦床现象”。艺术家、批评家、策划人一旦进入这一展览效应中即不能自拔,只能随着一个谁也说不清的、象永动机一样的“自动力”去拼命转动。就好像大家都上了蹦床,你想停下来思考也不行,必须得一起“蹦”。除非你下去,但是这也意味着你要下课。几个展览不见面,一两年不参加展览,就意味着此人在当代艺术中消失了。自甘寂寞和反潮流在当前似乎比以往都要艰难。因为,官方反官方、体制反体制、保守反保守等界限比任何时候都模糊了。
出于对1980年代及之前的集体主义、群体意识的逆反,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另一个流行批评话语是极端的强调艺术家私人生活经验。这是一种“集体vs个人”的另一个二元论的叙事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艺术“国际化”的冲击下,这种模式更为流行。西方的一位很有影响的现代性研究学者,安东尼·吉斯登(Anthony Giddens)说,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性质即是全球化影响下的“扩张性”和个人失落带来的“私密性”之间的日益增长的距离。[32]这两个极端现象的描述又使我想到了西方传统的二元论。不论它在中国的具体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它是否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艺术批评,但至少这一思考角度似乎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叙事中已经流行。在评判艺术作品时,越是“个人”的就越真实。这种个人视角排斥艺术作品与历史、群体和整体文化的联系。似乎全球化必定带来全球的、国际的“个人身份”化,即全球化必定使中国的艺术家变为全球村居民的一员(global citizen),说着非常“私密性的”但又标准国际发音的普通话。但问题是,是否中国大都市的每日崛起的商厦、银行和旧社区的消失,这种全球化和都市化的扩张已经彻底地摧毁了中国的传统社群意识和儒家的社会关系模式,从而致使个人唯一能够保留的是记忆的碎片和私人的日常生活经验?那些现代都市景观是否可以等同或抹掉中国人从小在唐诗、宋词、红楼梦中所塑造的记忆空间?频繁的国际交流对话的结果是否就自然意味着国际身份性的形成?为何中国人到国外必须要建一个唐人街或中国城,难道只为商业和生存的需要吗?难道它不也表现了中国人对传统、历史文化以及社群意识进行复制和再现的欲望吗?不论它是否低俗并体现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它是一种顽强的记忆空间的物质化再现。我要质疑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中是否有那种西方意义上的“个人化”与“集体”的对立。80年代的宏大题材和理想主义的叙事是否就没有个人的因素?而是否90年代以来的大量的以个人家庭、小生活环境为题材的绘画和摄影作品中就没有“集体”的表现意义?事实上,中国特定的历史文脉和当下情景决定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humanism)这一西方二元对立的范畴在中国情境中的特殊意义。当中国文化人和艺术家运用这一对立概念时,他们的原本意义可能已经被互换了。比如,文革后的“人道主义”文学和绘画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艺术可能是在强调某种“个人主义”的东西,比如真实的个人感情、直接的美感和自我风格等等。而1990年代以来的所谓的“个人主义”的叙述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的发明和传播的产物,是市场和博物馆策划系统所寻找的对象。“个人的”题材在这里大多被看作为“人道的”或“人权的”的等同物。
不论这种“集体”vs.“个人”、“理想”vs.“现实”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描述方式是否合理,至少1990年代初以来这种对极端“个人化”的叙事解读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空间叙事的平面化、琐碎化和去宏大性。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掉入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话语中,同时失去了对自身历史文脉和当下的特殊性的关注热情。这无论是对建树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对中国的现实的表现方面都是一种负面力量。比如,在那末多的video 作品中出现的大多是个人身边的影子。少有表现那些迅猛地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巨大冲击的“宏大”题材的作品,如表现三峡大坝或都市变迁的“巨片”。张大力和王晋的早期作品就有这种倾向性。不一定非得是用写实纪录片形式的去表现,完全可以用观念性的抽象性的或数码媒体的形式去表现。但关键是我们没有这个热情。可对于后人来说,这是多莫千载难逢的题材呀。
最近几年来,中国女性艺术家越来越引起国际性的特别关注,一些讨论也明显透露出西方女权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的影响。即,将中国女性艺术家放入到一个类似西方女权主义的叙事结构中去讨论:少数民族(女性)和统治阶级(男性)的阶级对立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不变的宇宙性的权力结构。在这种修辞中,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总是表现一个极度个人化的、通常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碎的事物连在一起的题材,而他们的对立面男性艺术家则类似于政治动物。 中国女性艺术家从怎样的角度去思考她们的创作题材和形式语言以及我们如何定义什莫是“中国女性艺术”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其复杂程度就象给中国的现代性和前卫艺术定义一样。中国女性艺术家当真要通过艺术创作来表现象西方女权主义那样的阶级对立似的观念和意识吗?这里总会有些不一样的东西。中国的传统男权社会可能比西方对女性更为压制。但是,中国女性艺术家对这一问题的表达方法和表现的目的可能是很不同的。为什么中国女性艺术家反复地使用传统女红材料,如针线、衣物、厨房用具等此材料来进行创作?秦一芬曾跟我说,很多西方女性艺术家问她这个问题。因为西方女性艺术家有意回避用这些表示传统女性身份的象征材料去创作。但是,中国女艺术家大概看到了二元对立类似位置的调换(少数民族变为统治阶级)并非他们的表现方法,亦非表现目的。而阴阳互相转化才是达到真正和谐的根本。所以女性“特质”本身并非是自己的缺陷,相反可能是转化的前提。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是否是东方传统哲学所倡导的宇宙和谐之体现?无论答案如何,有一点可能是清楚的,那就是西方女权主义的两极对抗理论,大概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女性艺术的视角和方法论。
又比如,我在2005年的《墙》展中试图尝试用“整一性”和现代性错位的角度分析当代艺术。三个展览主题:历史、景观、美学都是在谈错位问题。我就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把仍是西方二元论的东西,像集体与个人、传统与现代、男人与女人等这些观点打破,换一种方法去看这些问题,用多维的空间意识去检验这些问题。比如,我把长城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当代艺术中,如何把古迹的空间符号转化为当代艺术的现实空间。有意思的是,不仅长城的古意在当代被
转化为中国现代性,比如中国人的现代身份的符号。而且,在如何看待这一符号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距。比如,长城的形象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民族的象征?西方学者一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认为中国人从自己的政治需要赋予长城以现代文化身份。但是,事实上,长城的民族形象是和中国血的现实现实紧密相关的,不纯粹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1931年在抗战爆发日本占领东三省以前,在中国历代的绘画和艺术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长城形象,为什么到30年代突然间大批出现在版画、电影、音乐、包括活话剧中?那是因为现实,是因为战争,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关头,长城自然而然就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它是具体形象、物理建筑在特定时期成为象征性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现代性在特定时期——30年代出现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当时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关于长城的形象多得很,所有重要的战争都在长城上发生过。后来,在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和近年的全球化时期,长城的意义总在修正之中。并出现了一个“长城话语”。它是中国现代性身份错位的证明。
如果用西方社会和美学分离的观点去解读中国20世纪艺术,会出现一种偏离,事实上,由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在叙事上偏重写实和社会题材的艺术,所以注重哲理、美学和语言探讨的写意式的类似西方“抽象”类型的艺术,受到了冷落和遮蔽。。
在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开始阶段,中国艺术家和文化精英所呼唤的新艺术(现代艺术)的形式和观念并不是当时活跃在欧洲的后期印象派、立体派和野兽派等等,恰恰是在欧洲已经成为保守主义和学院主义的古典写实主义。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的等人在1920年代所倡导的“美术革命”论都主张用西方的现实主义去拯救中国颓废的文人画,[33] 而西方的现代主义则被视为和文人画同样颓废的没落艺术。 [34]虽然,这种观点并不为所有20世纪的艺术家和艺术流派所认同。但是,显然这种观点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主流叙事的价值标准。所以,三十年代的决澜社、林风眠、刘海粟、庞薰琴等人的创作,80年代以来的现代水墨和接近西方现代主义形式的艺术现象,包括“无名画会”在这种主旋律的叙事模式中(不论是在艺术史书写中,还是在艺术市场中)都沦为边缘艺术现象。 相反,在各种类型的“救亡图存”口号的感召下,现实主义艺术成为拯救中国的正统方法。但是,悲哀的是,这种拯救总是最终沦为堕落与媚俗。比如,1930年代左翼木刻运动转移到延安后,逐步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它得到了“喜闻乐见”和“民族化”的认同,却失去了早期的真诚和天真。1979年出现的“伤痕”现实主义,是对文革的控诉。但是,由于它没有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意识,最终只能走向悲怨和乞怜。并且,最终必然回归矫饰并和重商主义的学院主义合流。1990年代初出现的犬儒现实主义以其“自嘲”和“玩世”姿态挑战英雄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其“流氓意识”的“反叛”形式获得了前卫的称号。它自认为抓住了虚伪现实的病灶,但实际上,它只不过从“伤痕”的抱怨“他人”走向调侃“他人”,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非理性的自恋情绪其实是“自我表现主义”的,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它的“自嘲”同样也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自我批判和反省之上,因为,他只批判别人,不批判自己。“自嘲”其实就是自恋和自怜的同义词。所以,“玩世现实主义”很快就滑进了轻浮、艳俗和恶俗,向利益时尚、江湖法则全面投降,最终陷在市场和后殖民文化中不能自拔。对整个20世纪和过去20年的各种流行现实主义进行审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所以不能自保晚节,主要是因为几乎所有这些时尚的现实主义艺术都是建立在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目的之上的。同时,他们也都是媚俗的,不是趋同于大众的通俗性,就是屈服献媚于某种文化霸权和市场权势。
今天当我们回首过去三十年的当代艺术,以及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用“启蒙”和“救亡”或者“逃避现实”和“关注现实”的简单二元对立的眼光去检验中国现代和当代视觉艺术的意义和本质了。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之下,上述现实主义的诸种流派,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关注现实的,是救亡图存的产物。而非写实的(一般被称之为形式主义的)的艺术则被称之为逃避现实的、甚至非本土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复制品。进一步,上述的那些现实主义流派更是理所当然地被看作为本土艺术的代表,尽管现实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是从西方[苏联]引进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波普现实手法对中国当代艺术影响也很大,但也是从西方来的,但我们很容易把它们看作是中国本土的现当代艺术。更早一些的还有,三十年代的左翼版画和延安版画,毛泽东时代的艺术,还有“文革”后的“伤痕绘画”、“乡土绘画”,甚至新学院主义的写实画、九十年代以来的各种后现代类型的调侃现实主义[简称“大脸画”]和拼凑图像的风格,统统都被认为是最能反映本土现实的艺术,从来不说它们是对西方艺术的模仿,因为他们的样式中带着中国人的面具和背景。但是,那些和西方主流的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接近的艺术现象,那些不直接反映中国的可视现实的视觉艺术则很容易被戴上模仿的帽子。比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艺术,象决澜社的艺术、“八五美术运动”中的理性绘画和“反传统”的观念艺术,抽象水墨和抽象画等,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的观念艺术[如我称之为“公寓艺术”的那一类],则很容易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类型的艺术,是对“舶来品”的模仿。如果星星画会没有对当时的政治压制进行反抗从而酿成政治事件的话,星星成员的那些占大多数 “形式主义”的作品恐怕都会被历史学家描述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模仿或者是个人主义的无病呻吟。无名画会的命运就是证明。在这种视角和偏见之下,在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叙事之中,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显然被边缘化了,它的中国本土现代性的本质也就更不能得到充分认识和研究。
虽然,西方现代艺术史在视觉形式方面的不断革命和批判的动力主要来自它的审美现代性的观念,而且大多数的现代主义流派的抽象表现和几何形式看上去似乎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和政治更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常常称他们为“形式主义”。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形式主义”者都极力宣称他们的抽象艺术具有精神性和社会性。马列维奇认为他的“至上主义”是真正的革命,比十月革命还要革命,因为后者是社会和经济的,它的“至上主义”是精神的。他们的抽象艺术甚至比后者更具革命性。这就是现代主义者们的天真所在。
他们不是没有政治观念,也不是没有再现现实的冲动。正像格林伯格所说,“现代主义绘画不是反对再现现实,而是反对再现现实的那种虚假的幻象式的三度空间再现的庸俗方法。”[35] 格林伯格认为,两度空间的平面性是绘画的本质,平面性是对理念(现实的本质)的直接再现。而现实主义是虚假的,媚俗的,因为他取悦于庸俗大众。同时,他又将抽象主义绘画原理从上追朔到柏拉图的理念说。 柏拉图说,现实是理念的影子,艺术是影子的影子。因为,在柏拉图时代,艺术意味着模仿视觉现实,所以他认为艺术比现实还低级。格林伯格向下则追朔到启蒙主义运动,认为抽象表现主义是启蒙运动的科学进步的结晶。所以,现实主义不是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的代表,相反是知识分子对大众庸俗趣味的屈服和迁就。也就是媚俗。应当说,这种现代主义的抽象形式对“现实真实”的超越实际上得益于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并且在五十年代达到高峰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哲学。由于,这是另一个复杂的大问题,我将不在这里讨论,留待以后论述。
所以,从西方的批评家和艺术家对他们的形式主义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多年来对“形式主义”的误读和偏见。 形式主义不是不关注现实,而是用超越了视觉现实的审美独立的方式去隐喻性地、线形地或者几何式地去“结构”现实。其核心是超越。超越是不媚俗的根本。超越的极限就是“形而上”。只有超越了视觉的“真实”诱惑和现实功利主义,才能达到形而上。
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之所以不相信这种超越,原因是我们受到多年的庸俗社会学的“反映论”的影响而不能自拔。我们只相信艺术可以反映现实,不相信艺术的现实是虚拟的、假的、艺术家再造的。由此出发,我们只信奉“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的结果是,在批评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时常常“用写实形式去对应社会内容,或者用社会内容去否定非写实的形式”。在这种庸俗社会学原理的支配下,任何形式中不直接表现“社会内容”的艺术都被看作空虚的形式主义,或者现代主义。 比如,“无名画会”的风景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就会被完全忽视。我最近详细地整理了无名画会的资料,它似乎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审美独立和象牙之塔的立场是相似的。但是,它们的纯艺术却是对文革政治艺术的逆反。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性的。
应当说,一百多年来说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认真全面地对现代主义进行研究和介绍。我们只是孤立地介绍一些流派,但是砍断了它们和社会体制以及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中,现代主义常常作为形式主义的代名词。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深入人心的中国,在主观客观、唯物唯心的对立范畴作为基本的思维定势的指引下,现代主义被看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产物,现实主义则被奉为反映现实真实的标准。虽然,在当代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再流行,但是,与现实主义联姻的波普艺术、摄影等形式仍然发挥着以往的现实主义的功能,在当代艺术市场和展览体制中大肆流行。
在西方现代艺术之中,抽象艺术之所以作为精英艺术的代表,与大众和商业的媚俗艺术对立,那是因为,现代主义尊重个人的、大师的创造性编码 ——抽象形式的不断革新。但是在中国,这种个人的精英式的抽象艺术却被视为无意义的,纯粹物质形式的空壳。所以,个人的创造性想象让位于再现和模仿现实,而精英的艺术让位于大众媚俗的趣味。抽象主义的本质是知识分子的艺术,它崇尚怀疑主义、崇尚和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性,尊重学科本位的天真品质,这些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和品格。但是,在中国20世纪的社会中,这些知识分子的品格不断地被扭曲,所以,真正的精英艺术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结论
以上,我们在理论比较中讨论了中国的“整一现代性”的背景、来源和特点,我们会发现,“整一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弥合了西方的美学、社会分离的原则,使艺术能够回到现实的人、环境和客观事物和谐统一的境界。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主旨。如果我们把这个主旨、西方当代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他在很多方面和东方哲学美学有类似观点)以及当下的文化经验整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新型的美学和艺术方法论体系。这也是二十世纪以来许多艺术家和理论家所为之憧憬的。“整一性”很可能成为新体系的方法论视角。
但是,另一方面,“整一性”又很容易成为权力体制和话语中心的工具,使它衍变为实用主义的话语,强迫部分服从整体。对付这个双刃剑,我们必须一方面坚持对体制和话语权的批判,另一方面,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在今天尤为重要的是,在扬弃“整一性”的负面因素的同时,整合建树起新理论,新方法论和新艺术体系。有人可能会问我,你在这里所议论的“整一现代性”是不是也要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原理?不是的,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只负责陈述我自己的思考逻辑,以及提出我认为有意义的问题和模式,以期促进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和争论。
注释:
[1]名为“多样的现代性:国际会议“,于2005年11月在威尼斯召开,该会议是为200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而召开的理论筹备会议,笔者参加了会议并宣读了论文“三位一体的现代性”。另2007年巴塞尔文献展的主题也是现代性和传统,见第十二届文献展出版物《文献展杂志2007,第一期:现代性?》,该期杂志收录了选自全世界不同刊物发表的的21篇文章,包括我的文章《中国的现代性和前卫艺术》;此外,2006年4月29日至5月1日在香港城市大学和中国中央美术学院联合召开的名为《反思:作为自我意识的文化冒险的中国现代性》的会议,来自美国和亚洲的二十多名学者出席会议。见宋晓霞编辑的同名文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
[2]2004年11月,一个名为“同时代性不等于现代性”的会议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召开。大约三十位来自全世界各大洲的艺术史家、文化批评家、哲学家以及策划人参加了为时三天的会议。会议将发言论文集结为一本文集,2007年底即将出版,杜克大学出版社,泰利·史密斯Terry Smith主编。
[3]在19世纪早期的乌托邦社会学家圣西门那里,“前卫”一词不单用于艺术本身,也用以形容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进步角色。“是艺术家作为先锋解救了你们,艺术辉煌的使命是调动社会中的积极力量,一种真正虔诚的力量,强有力地推动着知识界前行。”引自理查德·V·韦斯特[Richard V. West] 《前卫:前进的步伐》一文。[Richard V. West,“The Avant-Garde: Marching in the Van of Progress,”in S.A. Mansbach, Standing in the Tempest: Painters of the Hungarian Avant-Garde, 1908-1930;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1, p.11], from Henri de Saint-Simon, Opinions Litteraires, Philosophiques et Industrielles, Paris, 1825]
[4]波吉奥利(Renado Poggioli)等学者探讨了西方前卫艺术如何将审美的现代性的最初原则转化为完整的前卫艺术的修辞学。彼得·比格尔(Peter Burger)从体制自我批判的角度描绘了审美现代性的历史作用。换言之,前卫先锋们追随了美学主义的基本趋势,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展现出不与日常生活同流合污的独特个性。见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Peter Burger,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p.15-20 ] 此外,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延续了波吉奥利对西方前卫艺术的基本分类的阐述,将前卫和现代性拓展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把波吉奥利描述的前卫艺术本质的四个组成部分拆解为现代性的五张面孔,并把后现代的一些特点也囊括进现代性之中。见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张面孔:现代主义、前卫思想、颓废、媚俗、后现代主义》,[Five Faces of Modernism, Avant - Garde, Decadence, Kitsch, Postmoder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此书更早的版本为《现代性的面孔:前卫、颓废和媚俗》。[Faces of Modernity, Avant - Garde, Decadence, Kits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但是,他们的基本出发点都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关,同时也与韦伯的学科独立的理性化说法相关。
[5] 比较典型的是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的纯艺术观念。在他的《前卫与媚俗》一文中,他将毕加索等人的抽象绘画看作与俄苏现实主义、好莱坞电影相对立的精英艺术,而后者则是媚俗艺术。[Clement Greenberg,“ Avant-Garde and Kitsch,”in Art and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6]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工程》,发表在《反美学》,Hal Foster编,西雅图海湾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Jurgen Habermas, “Modernity - An Incomplete Project”, Hal Foster, ed. The Anti - 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Seattle: Bay Press, 1983, p.4.]
[7]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工程》,发表在《反美学》,Hal Foster编,西雅图海湾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Jurgen Habermas, “Modernity - An Incomplete Project”, Hal Foster, ed. The Anti - 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Seattle: Bay Press, 1983, p.9.]
[8]这比较完整的描述了韦伯的这一学说的著作为,彼得·比格尔的《现代主义的倒塌》一书,其中“文学制度与现代性”一章对这一现代“分立”所造成的专家文化和公众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均有详细的阐述。[Peter Burger, The Decline of Modernism, trans. Nicholas Walker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9]参见邦尼·麦克多卡(Bonnie S.McDougall)《西方文学理论在现代中国》,东京东亚文化研究中心1971年版,第 196 - 213 页。[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Tokyo: Centre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71, pp. 196 - 213]
[10]麦克多卡(McDougall)的关于前卫的定义,来自Renato Poggioli在1968年出版的《前卫理论》。她对前卫的界定事实上源自Poggioli关于前卫的四要素:行动主义、敌对主义、虚无主义和自我中心。她由此得出结论:由于缺少这四个要素中的两个甚至更多要素,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不能称为前卫运动。Peter G.Christensen曾联系Poggioli的原文,总结出Poggioli关于前卫的四要素的定义:1.行动主义:沉迷于“崇尚活力、行为意识、运动激情和超前向往”的自我冲动;2.敌对主义:对现存的所有事物抱有敌对态度;3.虚无主义:一种“卓越的无政府主义”,“不但能够从运动的胜利中获得喜悦,更从克服障碍中获得更大的快乐:捕获对手,摧毁进行途中的路障等等”;4.悲剧情怀:在一种集体的“超越现实经验的行为主义”运动中,去“直面那为未来的成功而冲动地奉献牺牲的自我毁灭”。参见《Poggioli,Burger和Calinescu眼中的颓废和前卫的关系》,《语言和文学》[Paper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22期,1986年春季刊,第209页。
[11]这种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历史延续性,在哈贝马斯对“现代”一词的语源学描述中显示的很清楚。他说modern的拉丁文原型是modernus,于5世纪晚期首次被使用,用以将已经成为罗马官方宗教的基督的“现在”和旧罗马时代作为异教的基督教的“过去”相区别。由于modern(现代)具有现代和传统的双重关联意义,所以modern(现代)在西方不断地被用来表示与过去的古典时代相关的“新时代”的意识,并以此将自己——“现代人”看作是从传统而来,是从旧往新转化的新人。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当5世纪modernus一词刚刚出现时,它与传统和过去的联系是很重要的。因为,作为刚刚成立正统宗教的基督教为了宣示它的正统性,有必要强调它的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它的悲怆而光荣的历史。而现在(20世纪以来),当我们再用“现代”这个词时,往往没有了它原始的“传统”意义,而更多地用以宣示与过去的断裂和新旧之别。因为现代是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现代是古代的复兴。见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工程》,发表在《反美学》,Hal Foster编,西雅图海湾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Jurgen Habermas, “Modernity - An Incomplete Project”, Hal Foster, ed. The Anti - 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Seattle: Bay Press, 1983, p.3-4.]
[12]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神州学会,《新青年》第三卷第6号 [1917年8月号]。
[13]举例而言,林风眠曾经说过,“艺术根本是感情的产物”,“一切社会问题,应该都是感情的问题”。林风眠:《致全国艺术界书》 [ 1927年,见《林风眠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19页]。他的作品《摸索》[1924]、《人道》[1927]和《痛苦》[1929]清晰地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路。在这些早期作品中深色的背景、扭曲的躯干和叙事意味的构图传达了现代主义形式下的人文氛围。
[14]《决澜社宣言》,《艺术旬刊》第一卷,第5期 [1932年10月号]。
[15]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第六卷,第4号 [1919年4月号]。
[16]参见拙作《论毛泽东的大众艺术模式》,《21世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73页。文章讲述了30年代前卫文艺运动是如何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转变为负载着群众革命使命的启蒙运动的。如毛泽东思想所述,思想进步的青年成为普通文艺战线工作者,并接受了革命再教育。
[17] 木刻版画运动,参见孙雪莉《鲁迅和中国的木刻版画运动,1929-1935》(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74年版。
[18]《梁秋实论文学》,《台湾时报》1978年,第234页。
[19]有关俄国和欧洲前卫艺术家志愿加入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事例,见Boris Groys《斯大林的整体艺术:先锋、美学独裁及其超越》,Charles Rogle 译,新泽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2年,12页。[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P12],及Igor Golomstock的《苏联艺术:the third Reich,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伦敦,Colllins Harvill出版社1990年版)。
[20]Yve-Alain Bois分析了俄罗斯前卫艺术的物质乌托邦动机,见《里奇斯基:一个物质乌托邦》,发表在《美国艺术》1991年6月号,第98-107页。
[21]见我的《论毛泽东的大众艺术模式》一文,《21世纪》1994年第6期,第61-73页。
[22]In the classic Chinese在中国典籍中,它表示带领军队冲锋的英勇将领。明代话本小说《先锋》常用以解释此词。明代《三国演义》中的一些句子,已经成为成语,包括“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23]有关 “现代” 一词在中国早期现代文学中的语义变迁的研究,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研究:中国20世纪历史和文学新思维的几点反思”,《剑桥中国史》现代部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1] 。 [Leo Ou-fan Lee, “In search of Modernity: Some Reflection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文中他解释了何为“新”,以及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新”和“现代”的关系。亦可参见李欧梵:《文学思潮1:对现代性的思考1895 - 1927》,《剑桥中国史》第12卷,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451-504页。
[24]Serge Guilbaut,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Abstract Expressionism,Freedom,And The Cold War《纽约是怎样偷了现代艺术观念的:抽象表现主义、自由和冷战》。
[25]见《中国现当代艺术史1985-1986》,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352页。
[26]参见《中国现代艺术展》画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7]见《中国新艺术Post-1989展》“政治波普”部分,香港汉雅轩1993年版。
[28]见Margarita Tupitsyn,《Sots艺术:俄罗斯解构力量》,纽约当代艺术新馆1986年版。
[29]见Boris Groys《斯大林的整体艺术:先锋、美学独裁及其超越》,Charles Rogle 译,新泽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2年,12页。[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
[30]我此现象写入《权力与共犯:政治波普现象》一文,《雄狮美术》第297期(1995年11月号),第36-57页。
[31]见Andrew Solomon文,《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1993年12月19日。
[32]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的自我与社会》[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33] Wu, Lawrence. “Kang Youwei and the Western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Art,” in Orientations Vol.21 No.3 March 1990 pp.46-53.
Pang Tao, ed. The Storm Society and Post-Storm Art Phenomenon. Taipei: Chin Show Publishing Co., 1997.
[34]这种论点可以在徐悲鸿和徐志摩的“二徐”之争中看到。徐悲鸿“我惑”,徐志摩“我不惑”。
[35]格林伯格,“前卫与媚俗”。Gereenberrg, “Avant-Garde and Kitsch,” in Art and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pp. 3 – 33.
|
|
|
|